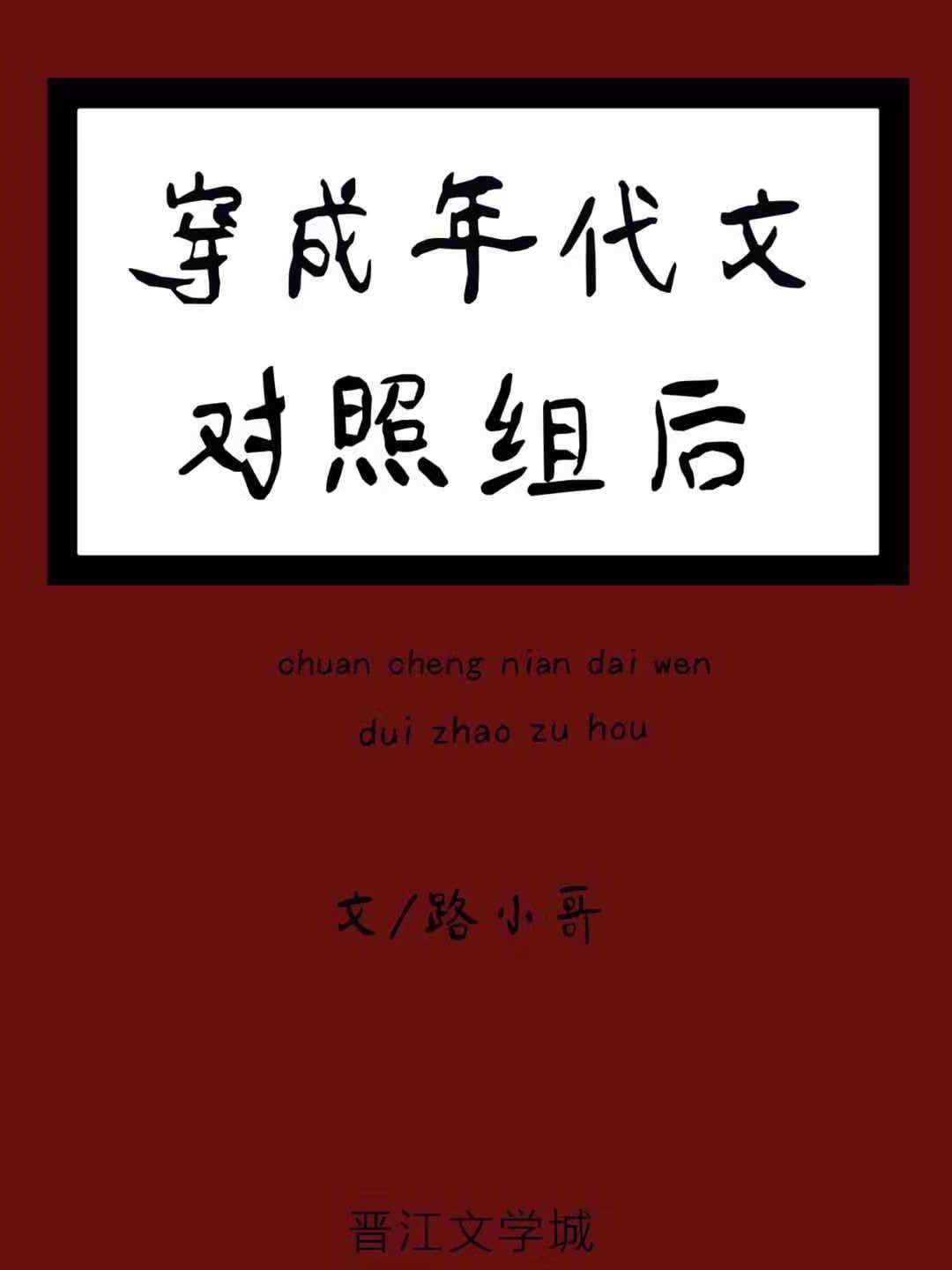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废铜价格回收价格表今天 > 第72章(第2页)
第72章(第2页)
净雯的声音是刻意放平稳的:“南地距京师数千里之遥,纵然八百里加急,一来一回也要花上小半个月,冯氏插翅也没这样的能耐。”
我点头,看方合:“确定是常年不断,没有错漏?”
方合极笃定地点一点头,从怀里掏出张纸摊开给我看:“娘娘放心,有账簿为证呢。”
我一看,那墨迹是新的,多半刚抄好没多久。
许是见我脸上有疑惑神色,方合继续说:“奴才是找了人混进宝芝斋去的,之后那人跟账房先生混熟惯了,才抄了这份东西出来。”
我定睛一看,密密麻麻一张纸的字迹,再一看那采买的日子,果然挨得很近。
压一压心头欣喜,问:“那人可靠吗?”
“是小回子的远房亲戚,且他并不晓得内里关节,再可靠不过。”
他是极伶俐的,也一向谨慎周全,我是很放心的,辗转片刻,伸指点一点他的额头:“办得很好。还是那句,凡事谨慎,银两随意支,宫中人多,该打点的地方也不必替我省,明白了?”
“奴才省得。”
挥手让他去了,长久的静默后,脸上笑意一点点漫上来。
净雯静静瞧我片刻,轻声笑:“方合当真得力。”
我亦笑:“是啊,他很机灵,懂得变通,也细致。”
“最要紧是待娘娘足够忠心。”顿了顿,换了郑重神情:“倘若直接跟皇上说,皇上未必肯信。”
我冷笑,却也点头了:“我想也是。况且冯氏如何能坐以待毙?能不借故托词?”
食指哧一声哧一声划过花梨木桌案,并不是多动听的声音,然而却分外让人警神。
净雯静默片刻,小声道:“积年之事,皇上不会提,知情人也多讳莫如深,宫中嫔妃更是无从得知。冯氏能这样张冠李戴,让皇上信了真是她,必定是有些缘故在的。”
“知情人?”我凝神一点点思索,缓缓道:“印寿海常年侍上,自然算得上是知情人,然而他连在我跟前都不敢露出话来,旁人自然更听不到半句。那么除了印寿海,能知晓前情的人,就只能是——”
猛一抬头,果然在净雯目中看到了同样的答案。
“会是那样吗?可为什么…?”
这话问得已有些语无伦次,净雯按一按我的手,道:“轻舟蒙面而来是为凑巧,那么曲子呢?是否太过凑巧了些?换了谁,谁能不信她是真的?即便不信,总有疑惑,会探究。皇上自然也不会例外。”一壁说一壁冷笑:“不过她这个张冠李戴,当真用足了心思,可见这么些年隆宠不断也并非毫无缘故。自然,想要登高呢,花再多的心思也不枉费。至于那一位…”手一伸指向颐宁宫的方向:“如何能不厌弃了冯氏?必定要的。”
厌弃只是表象,私相授受才是正经,且当年的事,事无巨细,还能有谁比太后更清楚?
可还是那句话,太后为什么要这样襄助冯氏?
净雯缓一缓神情,道:“此事可留着慢慢查探,眼下娘娘还是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挑破她那层面皮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