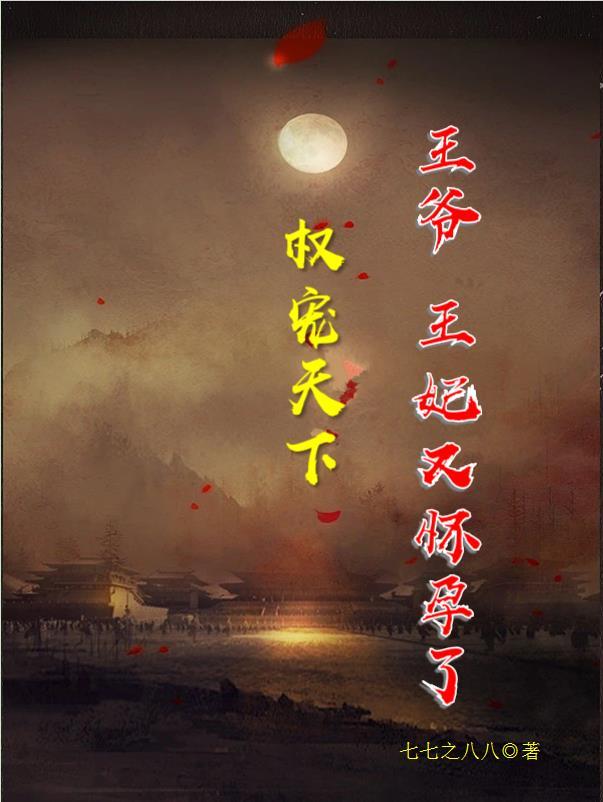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贵族学院里的万人嫌崔判全文 > 第151章(第1页)
第151章(第1页)
>
季殊对后一个倒是有了些兴趣。她在罗莱拉的高中时期曾经接受过慈善组织的捐赠,时隔多年,她也想去看看组织发展得如何。
两个人收拾了一会儿,即刻出发。
弗兰德开放日热闹非凡,停车场里停满了豪车超跑,相比起来,路家的豪华轿车在这里只能算是普通。
路源清的妈妈在兰顿和合伙人开了家律所,接过大大小小不少案子,在业界小有名气。路源清因为不想学法,又想逃脱家里的管教才在大学选了计算机,被她家流放出国摸爬滚打以后灰头土面,最后还是决定灰溜溜滚回她妈妈的公司里实习。
她家里不算太大富大贵的人家,但也在弗兰德有头有脸。一路过去跟不少人打了招呼,有同届的,也有认识的学弟学妹,还有她家里公司的实习生。
开放日校内禁止车辆通行。季殊跟她一起扫了辆单车骑行,这也是她头一次发觉弗兰德学院这么大。从前她活得一直很紧张,也从未像其他新生一般好好逛过校园。
光是围着学院内的人工湖她们就骑行了二十多分钟。季殊以前在这里的草坪上睡过午觉,现在依然能看到不少三三两两睡觉的学生和情侣,无人机在空中倾斜着飞过,还有人拿着自拍杆在做直播。
骑过礼堂和天使喷泉、教学楼和A09,然后是食堂、体育场和放映厅、温室花园和建校之初建立的校长温顿的铜像,最后是废弃的实验楼和综合活动大楼。
季殊累得气喘吁吁。两个人中午用自带的三明治解决了午餐,晚上则跟着人流排队进了食堂刷卡打饭。
用路源清的话来说,就是没想到自己还有能当回高中生的一天。
傍晚时分弗兰德涌进来了很多人,他们举着摄像进了放映厅。路源清拦住了一个人打听,一个女生对着镜头给她介绍,这是“圣地巡礼”。
“圣地巡礼?”路源清也懵了。
“今天晚上五点半至十点半播放图书馆典藏区的录像带,能看到弗兰德往届学生们出演过的音乐剧剧目。”女生耐心地解释道,“很多知名校友都在典藏区域里,而且这次放映允许录像,所以很多人都来摄像打卡。”
她兴致勃勃道,“你们知道季殊学姐吗?现在的反霸凌组织前身就是她影响成立的,青少年身心健康保护法案的修订也受她的影响推行。她前些年意外去世,SNS上很多悼念她的人们自发地组成了队伍,准备在弗兰德校庆开放日这天‘圣地巡礼’,看看她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
季殊莫名有点脸热,她咳嗽一声,倒是路源清起了兴致。她准备进场观看,但是被告知场内席位早就预定满了。
“这次的组织慈善募捐礼品是学姐的表演复刻录像带,”女生好心告知她们,“等募捐开场了你们可以去教堂那边看看。不过最好早点过去排队,数量有限,听说好多人已经在网络上发帖开始炒周边价格了。”
季殊不知道自己那出场不到半个小时、演技拙劣的录像带有什么好炒的。但是一想到那么多人要看到她的录像,她内心忍不住尴尬到隐隐抓狂。
她好一会儿才恢复淡定,跟着路源清去排队。队伍很长,排了十来分钟季殊终于看见教堂的大门,门口有一个隐约熟悉的人影在发放入场纪念券和维持秩序。
又前进几名,季殊才看清了那道高挑清立的人影。
谢周霖穿着黑色的大衣,围着围巾,戴着黑色的手套和眼镜,站在门口,垂着睫毛,逐个派发入场券,递签名表。
不少女生借着排队的名义围着他尝试递自己的联系方式,但都被他无视。他只专注着自己手头的工作,好像其他人一概看不见一般。
几年不见,他的身高又长高了一些,只是似乎更加清瘦,脸色青白。举止依旧矜贵端重,面对外人时眉眼冷淡疏离,但分寸得体。只是身上多了一股萦绕着挥散不去的阴郁之气,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虚无、脆弱的空洞,将自己严实地裹在外套之中,如同害怕被人发现空空如也、一片废墟的内里。
季殊看见他呼吸顿了一瞬,很快如常。
排队到她的时候,谢周霖把签名表递给她,声音疏淡平稳,“请在这里签名。”
季殊在签名表上签了靳铭泽的名字。
@无限好文,尽t在
谢周霖将纪念券递给她,两个人的指尖擦过,没有任何停留。谢周霖的视线没有感情和停顿地从她的脸上划过,转向下一个人。
季殊倒是注意到他衣领间的银色十字和耳朵上的豁口。
那豁口明显是枪击造成的。难道在这几年里,他被卷进党争,不慎受到枪击受伤了吗?他又是什么时候信教的?
路源清打断了季殊无所事事的脑补。她拉着季殊来到教堂找到空位坐下,给她八卦门口的男人。
“你知道他吧?首相谢汝云的儿子谢周霖,”路源清坐在她旁边小声说,“三天两头上《NEWTIMES》的就是他。前些年他去疗养院住了半年,出来后一边上学一边在他妈妈的辅助下从政,现在已经进了议会,近两年风头可大呢,都说他要走谢汝云的老路,外头还有押他能在三十岁之前当上民主党党魁的。”
“……又不是皇室世袭。”季殊咕哝了声,突然想起什么,“他现在还在兰顿活动?他的大学不是塞弗林理工吗?”
路源清拍拍大腿:“你也知道这个八卦啊!”她眼睛里燃起光,语速加快,“当年学姐和他原本是一对情侣,两个人都申请了塞弗林。学姐意外身亡后,谢周霖便放弃了塞弗林的项目,留在了首都的帝国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