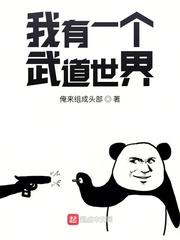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金主追妻 > 第105章 余烬(第1页)
第105章 余烬(第1页)
“疼就说话。”
“”
符骁还是没说话,他看着自己被死死钳着的手腕,只垂着手。
他觉得很累,不想说话,也不想面对很多人。
“你快松手!”
直到池御去拽厉盛的手,符骁这才缓过神,慢慢站起身。
“我去隔壁,把手放开。”
符骁的声音平缓,他没有挣扎,等着厉盛松手。
“滚开。”
厉盛一只手攥着池御的手腕往一旁甩,一边钳着符骁的手腕往外走。
“你就这么忍着他。”
厉盛抬起符骁的手腕,一只手扣着,把人撞在玻璃上。
剧烈的撞击,玻璃震了一下,符骁皱眉,腰半天直不起来。
他穿得单薄,突出的骨头硌得他生疼。
住院期间,营养全靠输液提供,病号服下空荡荡的直灌冷风,符骁的骨头在薄薄一层皮肉下,格外突显。
他的手腕周围一圈淤青,他直直对上厉盛的双眼,也不喊疼,只说了一句。
“他是我弟弟。”
符骁偏头看了眼身后昏迷的父亲,也像是在说给他听。
“你是不是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厉盛不依不饶,手里攥着签证,一拳砸在玻璃上,震得符骁头晕。
“有什么也结束了。”
厉盛的劲儿很大,池御被甩到一旁,尽管抓住了床沿,后背还是砸到了机器上,疼的不停地抽气。
他一边暗骂疯子,一边捂着后背跟了过去。
他自然跟不上气急败坏的厉盛,他先是看到符骁被压在玻璃上,又听见符骁的声音。
符骁说结束了。
池御定在原地,忘了要把厉盛推开,忘了跟过来是想和符骁解释。
但是他又能解释什么呢
符骁很平静,像是暴风雨前,在海平面上振翅的鸟儿。
他飞得不高,他贴得离海平面很近,他自知上不了岸。
他的羽毛被上涨的海水浸湿,他的鸟喙被翻涌的浪潮敲打。
只需要最后一朵浪花就可以吞没他,他离岸太远。
“其实没有一个月了。”
厉盛贴近符骁的脖颈,观察着他的表情。
“葬礼结束,就跟我走。”
厉盛把签证硬塞进符骁的手里握紧。
鸟喙被打湿,咸湿的,说不清是海水还是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