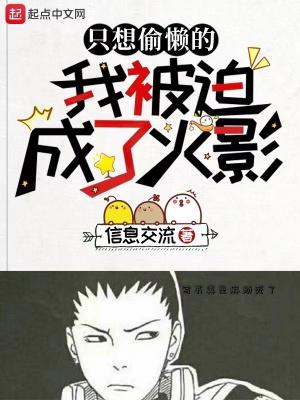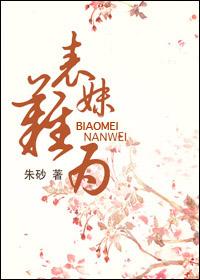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厌骨性肿瘤定义 > 第17章 赠金丹(第1页)
第17章 赠金丹(第1页)
商影云整个身子都种地里,如今却拔出个脑袋出来,像先人凿井,赶忙喊后人享福那样欢欣。
“望枯!这会儿坑都填好了!快跟上啊!”
望枯:“来了。”
与风浮濯萍水相谈闲话,素是前言不搭后语,又少有回音。
望枯自认风浮濯碰着自己这不记事的,是他福分。
风浮濯也跟上,忽而反将一军:“那望枯姑娘呢,为何会来此地。”
望枯大言不惭:“先前在皇宫背尸犯事了,被他们抓回磐州审讯,需途经祉州,所以来了。”
风浮濯听罢,再不多语。
商影云东瞧西看:“一个人嘟嘟囔囔什么呢?快些进来,指不定能赶在子时前找到出城路。”
望枯身轻如燕,学着僵尸双脚并拢的模样,屈膝一跳,就此坠入坑中。
头顶亘古月渐行渐远,但望枯身后却跟着挟来皎洁的佛,因此她每行一步,都有这盏长明灯为她画影子。
前头那些开路的士卒们,也算劳苦功高,手中却独有一把旺火,人人摸了个遍。谁人哼哧一嚏,火也灭个彻底,士卒们在甬道中争相推搡。
风浮濯暗自呼出一缕风,渔火点大的星子复燃成簇,还亮堂百倍。
商影云哪知有神帮扶,气息再稀薄,也能被他掰开了讲:“祉州有佛祖庇佑果真不一般啊,阿蓑落这三尺高地儿竟毫无损!阮瑎就不行了,人还在前头躺着呢!哎哟——”
最后这声变调,不往十万八千里外去,而逃入望枯的耳——军鼓都无这般震人,险些以为他遭了天大的罪。
而实则,只是前方何人停下,苦了他这吊于队伍最末却不看路的人,商影云前脚踩人鞋,后脚就翻成车轱辘,就此百转千回,一头栽进前人背上。
人们乱成河,湍急直下,再覆水难收。
风浮濯只顾抢回望枯一妖,但又庆幸是率先将她抢回。
——望枯咬他事小,不论名节与否,他都可将此烂进棺材里。可这些男子,一身铜骨,若不慎跌入其中,望枯如此娇弱,恐怕又要落下三两道疤。
他想到此处,面不改色放出结靡琴,命其再往臂上引伤一刀——即便女子尚在人间低人一头,他理应垂怜,却也不该以此佛身,窥度苍生。
望枯见他如此,轻捻裙衣,灵动翩跹。
望枯:“仙君,我身上并无新伤啊。”
那他为何又要自添伤口?
风浮濯一如寻常:“好,结靡琴倒是长进了。”
莫非,是怕结靡琴弦化为利刃的风会殃及到身旁望枯?
望枯:“……”
她不明白,风浮濯行事为何总有莽撞。
非他所想,为黑;为他所想,即白。
像是,从未有人告知风浮濯,他也为此间一笔循规蹈矩的浓墨,氤氲青天,御风万里。
但行错事,也无人唾弃。
商影云连滚带爬退居风浮濯身侧之处,哭丧着眼,煞白着脸:“完了,完了完了,这下真完了……”
望枯:“前路如何了?”
商影云:“找着阮瑎了,还找着好些活人,但……”
能让商影云难以启齿,已是惹人惊惧。
商影云吞咽口水:“这些活人,埋地多日,饿极了眼,趁阮瑎昏迷不醒,便将他腿肉割下……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