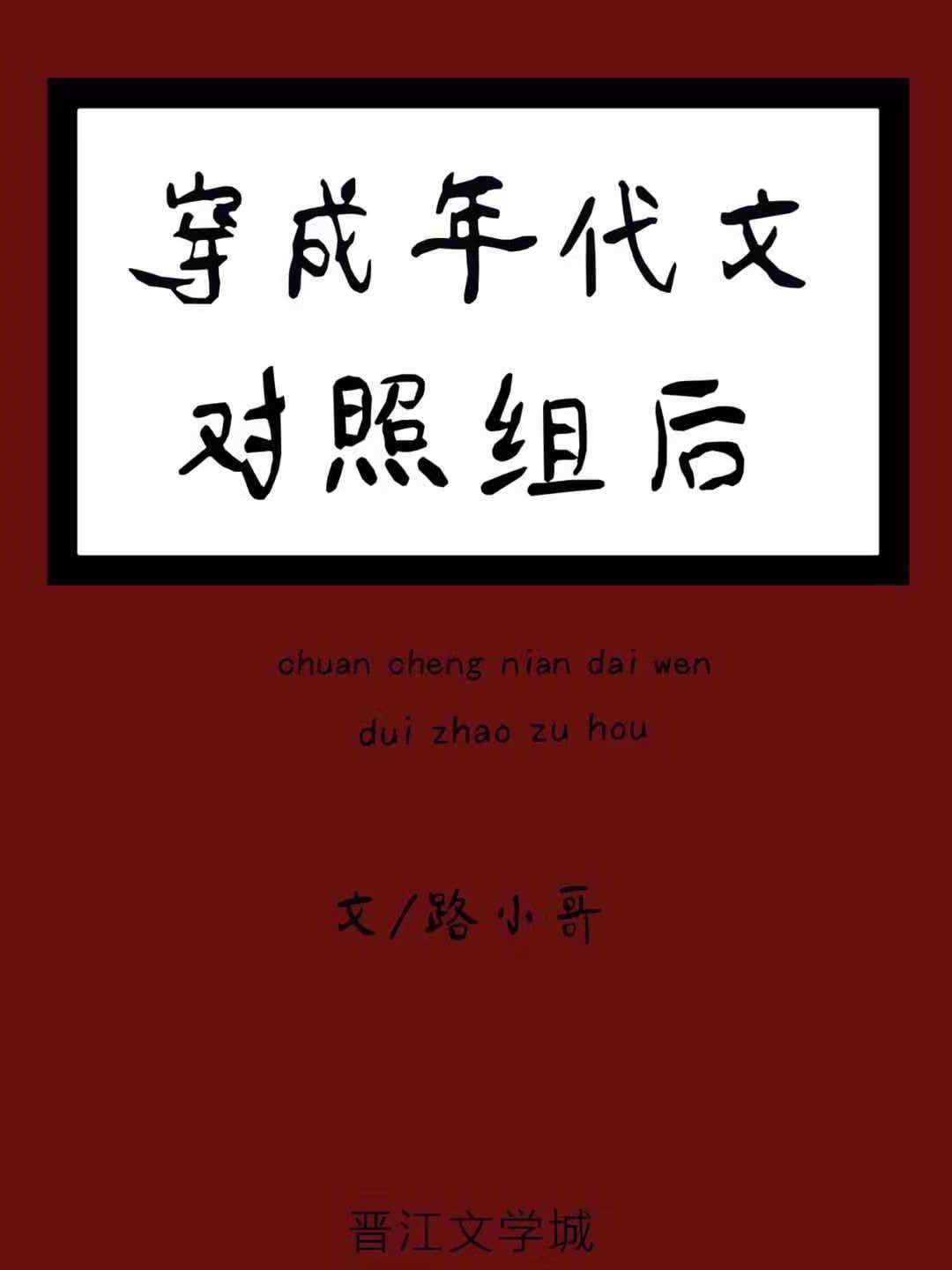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得半日之闲 可抵十年尘梦 > 六 中华腌菜谱 日青木正儿(第1页)
六 中华腌菜谱 日青木正儿(第1页)
译序
这是日本汉文学者青木正儿所著。青木著作有《中国戏曲史》,已译成中文,所以在中国也颇闻名的,前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现已退休,今年七十六岁了,还在著书,都是关于中国的,我所得到的有这几种,如《华国风味》《中华名物考》和《酒中趣》,都是很有趣味的著作。今译其《华国风味》中的一篇,原名只是腌菜谱,为得明白起见特加二字曰中华,是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所写,距今已是十六年了。槐寿译竟记。
(一)榨菜
以我的很浅的经验来说,中华也有相当可以珍重的腌菜。我最先尝到的,是北京叫作榨菜的东西。上海称它作四川萝卜,所以这似乎是四川的名物,可也不是萝卜,乃是一种绿色的不规则形状的野菜,用盐腌的,正如名字所说,是经过压榨,咬去很是松脆,掺着青椒末什么,有点儿辣,实在是俏皮的。
我初次知道这个珍味,是在初临江南的时候,在上海的友人家里,作为日本料理的腌菜而拿出来的。自此以后深切的感到它的美味,乃是后来在北京留住,夏天的一日里同了同乡友人到什刹海纳凉,顺便在会贤堂会饮的那时候。油腻的菜有点吃饱了,便问有没有榨菜?跑堂的连答了三声“有有有”,就拿了从冷藏库里刚取出来冰冷的、切碎的碧绿鲜艳的一碟。很可以下酒,以后到来的几样菜都叫堂倌拿走了,老是叫要榨菜,要了好几回,这才痛饮而散。
(二)虾油黄瓜
我从朝鲜经由满洲到北京去的路上,想起来是在山海关左近的一站。有一种什么东西装在小小的篓子或是罐里,大家都在那里买。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想来总是北方名物吧,我也是好奇,便也买了一个。木刻印刷的标签上,看不很清楚的写着“虾油玉爪”。虾的油是什么东西呢?至于“玉爪”,更加猜不出是什么了,心想或者是一种盐煮的小虾米吧。便朝着篓子看,同车的日本人也伸过头来看,说这是什么呀。答说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呢!说是不知道就买了么,便大笑一通。
到了北京之后,打开盖来看时,这却很是珍奇。是一种盐渍的没有像小手指头那么粗的黄瓜,满满装着,像翡翠的碧绿。要得这样一篓--说是篓却是内外都贴着纸,涂过防水的什么东西--小黄瓜,以我们日本人的常识来说,不知要从几百株的藤上去采摘,而且这样小的黄瓜除了饭馆里用作鱼生什么陪衬,才很是珍重的来加上一两个,算是了不得。于是才知道,从前认作“玉爪”的原来是“王瓜”之误,便是日本所谓黄瓜。虾油者似乎就是盐腌细虾腐烂溶解的卤汁。后来留心着看,此物往往用作一种调味料,譬如我们叫作成吉思汗料理的烤羊肉,就必须用此,但是因为有一种异样的气味,所以对于日本人是不大相宜的。用了这种卤汁浸的黄瓜,味道很咸,不能多吃,但是当作下酒的菜却是极妙的。回国后过了十多年,偶然有一个在上海的友人,托人带了两瓶这东西给我,我很高兴能够再尝珍味,赶紧拿来下酒,可是比起从前在路上所买的,却没有那新鲜的风味,不觉大为失望。现今想起来,觉得那时胡乱买得一篓,真是天赐口福了。
(三)笋干冬菜
从九江走上庐山,再从山的那一面下来,住在海会寺里。当地山僧拿出来佐茶的有一种笋干,很觉得珍奇,便拿来尽吃。到了第二天出发的时候,和尚在一个旧坛里取出那笋干五六根,又取藏在同一坛内的盐腌的干菜包,上面再包上荷叶,送给我道:“这样用干叶包着,存放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变味,而且这菜也可以吃。”我把这包很珍重地拿回日本,对着二三友人常骄傲地说,这是庐山寺里所制的名物,市场上没有得卖的东西,足以称作珍中之珍。这是怎么做的?因为言语不很能相通,不曾问得。好像是用嫩笋盐煮了,随后晒干,拿来细切后闲吃,有一种说不出的风味,是茶人(译者按:讲究茶道的风雅人称为茶人。)所喜欢的一种食品。
按清顾仲清《养小录》里笋油这一条里说,南方制“咸笋干”的时候,其煮笋的汁因为使用旧的,所以后来简直同酱油一样,而且比酱油还要好;山僧每常使用,外边极少能够看见。那么这笋似乎先用盐水煮了晒干,和腌菜略有不同,但是煮汁比酱油更鲜,这笋的所以如此鲜美,正是当然的了。
上面所说包笋干的那种干叶,在南方乡下的茶店里,也有拿出来佐茶的。在北京也有这种同样的东西,称作“冬菜”。不过南方用青菜所做,北方乃是用白菜罢了。北京把它细切在吃一种名叫馄饨的面食的时候,用来作料,嚼起来瑟瑟作响,很好吃的。
从前我们京都北边鞍马的名物有“木芽渍”的一种食物,从古代镰仓初期的显昭的《拾遗抄注》,直到江户时代都散见菜谱,似乎很是有名。但是不知何时却废止了,现在只能买到一种并不高明的土产品,叫作“木芽煮”了。实在是无聊得很。据雍州府的酿造部里说,这木芽渍是在春末夏初,采取通草叶,忍冬叶和木天蓼叶,细切混和了,泡盐水内随后阴干的。大概与北京的菜有相似的风味,而材料是用的野菜,想必更是富于野趣的了。
(四)泡菜酸菜酱菜
腌白菜最有滋味的,要算是北京“泡菜”。这是用白菜为主,和其他菜蔬,泡在和有烧酒的盐水里,雪白的白菜配着鲜红的辣茄,装在盘里很有点像京都的“千枚渍”的模样,味道清雅,宜于送饭,也宜于下酒,风味绝佳。
白菜做成的珍品,北京还有一种“酸菜”。这略为带有一种酸味,可是里边并不用醋,似乎是同京都的“酸茎”的做法一样,盐水泡后,自然发酵成为酸味,但是这不像酸茎的用重物压着,柔软多含汁水,大概是泡在盐水里的缘故。平常吃“火锅子”的时候每用这个,煮了也仍是生脆,比吃煮熟的白菜在味觉触觉上都感到更为复杂,很有意思。
河北省保定的酱菜也是名物,可是盐味太重,吃了觉得嘴都要歪了,还不如北京近郊海甸村所出产的来得味道温雅。北方酱菜大概都像我们的“福神渍”似的切碎了再腌,好像是装在粗布口袋里去腌的样子。然而长江沿岸九江地方的名物酱萝卜,都是同日本一样的用整个腌,其萝卜像小芋头似的小而且圆,看了也很可爱,味道也和日本的相似。日本的酱菜大概是古时的留学僧人学来的美妙制法。实在北京也有同样的物品,不过猜想这或者是从南方运来的也未可知。
(五)酱豆腐糟蛋皮蛋
酱菜里边最是珍奇的是“酱豆腐”,便是豆腐用酱制成的了。(译者按:这种酱豆腐,所指的是别一种,实际乃是北京所谓臭豆腐。)外皮赤褐色,似乎是腐烂了的,内中是灰白色,正像干酪(cheese)稍为软化一点的样子,有一种异臭,吃不惯的很难闻。但是,味道实在肥美,仿佛入口即化,着舌柔软,很是快适。从各方面看来,这可以称为植物性蛋白质的干酪吧。吃粥的时候这是无上妙品,但当作下酒物也是很好的。和这个同类的东西,还有糟豆腐,就是豆腐用糟制的。这在材料的关系上带着甜味,也没有那样臭味,只有酒糟的气很是温雅,但是当下酒的菜来看,或者还是取那酱豆腐吧。
糟制食品里可以珍重的是“糟蛋”了。这是用鸭蛋糟渍,外观和煮鸭蛋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用筷子去戳,壳是软当当的随即破了。里面黏糊糊的,像是云丹(海胆黄)似溶化了的蛋黄都流出来了。用筷子蘸了来吃,味道也有点像云丹,甚是鲜美,不觉咂舌称美。
说起糟蛋,势必连到“皮蛋”上去。皮蛋一名松花蛋,在日本的中华饭馆也时常有,蛋白照例是茶褐色,有如果冻,蛋黄则暗绿色,好像煮熟的鲍鱼的肉似的。据说,是用茶叶煮汁,与木灰及生石灰,苏打同盐混和,裹在鸭蛋的上面,外边洒上谷壳,在瓶上密封经过四十日,这才做成。我想这只有曲店或是做豆豉的老板,才能想出这办法来。总之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功绩了。不晓得是谁给起了松花的名字,真是名实相称的仙家的珍味。北京的皮蛋整个黄不是全部固体化的,只是中间剩有一点黄色的柔软的地方,可以称为佳品。因此想到是把周围的暗绿色看作松树的叶,中心的黄色当作松花,所以叫它这个名字的吧。此外还有一种“咸蛋”,是煮熟了盐腌鸭蛋,但是很咸,并不怎么好吃。但是将鸡鸭蛋盐腌了,还想出种种的花样来吃,觉得真是讲究吃食的国民,不能不佩服了。
(六)腌青菜
在江南作春天的旅行,走到常熟的那时的事情,从旅馆出来,没有目的的随便散步,在桥上看见有卖腌青菜的,似乎腌得很好。这正如在故乡的家里,年年到了春天便上食桌来的那种青菜的“糟渍”,白色的茎变了黄色,有一种香味为每年腌菜所特有的,也同故乡的那种一样扑鼻而来。一面闻着觉着很有点怀恋,走去看时却到处都卖着同一的腌菜。这是此地的名物吧,要不然或者正是这菜的季节所以到处都卖吧,总之这似乎很有点好吃,不觉食欲大动,但是这个东西不好买了带着走吧。好吧,且将这个喝一杯吧,我便立即找了一家小饭馆走了进去。于是将两三样菜和酒点好了,又要了腌菜,随叫先把酒和腌菜拿来,过了一刻来了一碗切好了腌菜,同富士山顶的雪一样,上边撒满了白色的东西。心想未必会是盐吧,便问是糖么?答说是糖,堂倌得意的回答。我突然拿起筷子来,将上边的腌菜和糖全都拨落地上了。堂倌把眼睛睁得溜圆的看着,可是不则一声的走开了。我觉得松了一口气,将这菜下酒,一面空想着故乡的春天,悠然的独酌了好一会儿。
有一回看柳泽淇园的《云萍杂志》,在里面载着这样的故事:飞喜百翁在招待千利休的时候,拿出西瓜来在上边撒上砂糖,利休只吃了没有糖的地方,回去以后对门人说,百翁不懂宴飨人的事情,他给我吃的西瓜,却加了糖拿出来,不知道西瓜自有它的美味,这样做反失去了它的本意,这样说了便很想发笑。我读了想起在常熟酒店里的一幕,不禁惭愧自己的粗暴行为,但是西瓜加糖假如是蛇足,那么腌菜上加糖岂不更是蛇足以上的捣乱么?若是喜欢吃用酒糟加糖腌了的甜甜蜜蜜的萝卜所谓浅渍者,东京人或者是难说,但是在喜欢京都的酸茎和柴渍的我,却是忍耐不住地觉得不愉快了,况且这又是当作下酒的东西的时候乎。
(七)白梅
可是我近年来在梅干上加糖来吃,也觉得有滋味了(译者按:这一节似乎是出了题,因为中国腌菜里没有梅子这东西,但是著者因为腌青菜加糖这事顺便说及,故今亦仍之。所谓梅干是指日本的盐渍酸梅,乃是一种最普通的也是最平民的日常小菜,平常细民的饭盒除饭外只是一个梅干而已。)这个因缘是因为我的长男住在和歌山县的南部,北方乃是梅子的产地,时常把地方的名物“封梅”去了核的梅子用紫苏叶卷了,再用甜卤泡浸,带来给我,偶尔佐茶,那时起了头。随后因了砂糖缺乏,封梅不再制造了,但是那种甘酸的味道觉得不能忘记,只在平常的梅干上加点白糖,姑且代用。这种味道的梅干,从前我在苏州也曾吃过。在拙政园游览,因为无聊去窥探一下叫卖食物的人的担子,夹杂在牛奶糖小匣中间,有一种广东制品记着什么梅的。便去买了打开来看时,里边是茶褐色的干瘪的小小梅子,吃起来酸甜多少带有盐味,很是无聊的东西。那里的梅干有好吃的,就是在日本的中华饭馆里也时常拿出来的东西,即是“糖青梅”,颜色味道都好,那的确是好吃。
日本人的对于梅干与泽庵渍(译者按:一种盐腌的长萝卜,福建有所谓黄土萝卜,用黄土和盐所腌,盖是一样的东西,泽庵是古时和尚,留学中国,所以是他从中国学去的。)的嗜好实在根深蒂固,从前所说给海外居留的本国人送去木桶,有相当数量,我到北京以后,和在住的同乡一同吃饭,就特别供给泽庵渍,像是接待新来客人似的。我在中国的时间偶然感冒躺了两天,喝着粥的时候也怀恋起梅干来,叫听差到东单楼的日本店里去买。下粥的菜酱豆腐和酱菜也是很好,梅干的味道却又是特别的。在中国似乎没有像我国那样的有紫苏的梅干,有一种不加紫苏用盐渍的叫作“白梅”,从古以来就制造着,也使用于菜料,这个制法也传到我国。紫苏是制造梅酱时这才加入,从古昔到现在都是如此,清初康熙年间的《养小录》卷上、《柳南随笔》续编卷三和近时世界书局的《食谱大全》第九编所记梅酱制法,虽然有点小异,可是加紫苏的一点却是一致的。那么现行我国的梅干制法,乃是将这里白梅和梅酱的制法合并了制造出来的东西,那么原虽是出在那边,可是可谓青出于蓝的佳品吧。我国古来的文化亏负大陆的地方很多,可是加以修改作出优秀的我国的文化来却有很好的智慧,这就是在小小的梅干上也看得出来,实在是很可喜的。
(八)菜脯
在中国没有听见过用盐加在米糠里腌的东西,泽庵渍这种东西的原本似乎也是没有。然而在萨摩地方(译者按:在日本南端,向来与中国闽广有往来),却有与泽庵渍类似的叫作“壹渍”的异样的渍物,尝在那地方出身的人的家里遇着这种食物,觉得珍奇,问其制法,大略是萝卜盐腌日晒,放在簟上揉了又晒,揉了又晒,装在瓶里封好放着。想起来好像是传授了浙江或是福建那边的“菜脯”的做法。这在《八仙卓式记》(《故事类苑》饮食部食卓料理条下所引)里记清国人吴成充(像是船主)在船里招待金石衙门(像是通事,即翻译)时的菜单,在《小菜八品》之中有菜脯,附有说明如左:
菜脯在冬月将萝卜一切四块,用盐腌一宿,次日取出晒干,放在簟上熟揉,又放入桶里,上边撒盐,次日取出照常的做,如是者四五日,瓶底敷稻草,搁上萝卜排好,再加稻草同样加上几重,乃加盖封口,隔些日子取食,用法与此地的小菜相同。
这个制法比我所听到的壹渍的说明,还要说得委曲详尽,那么萨摩壹渍的所本也就明白的可以看出是在这里了。原来从前萨摩是介在琉球中间,把中华的事物种种传来日本的地方。明和年间(一七六四至一七七一年)萨摩藩主岛津重豪擅长华语,著有《南山俗语考》五本,讲解中国语,刊本至今尚存。宽政年间(一七八九至一八〇〇年)的《谭海》卷八说起“狗子饭”,便是将米装在小狗的肚里整个烧熟了,曾经盛行过这样的中国料理,也曾进呈藩主,所以那地方与中国事物的交涉相当密切,现在我猜想这菜脯的制法传到了萨摩变成壹渍的想法,也决不是牵强附会的吧。
与这个相类似的渍物在我内人的乡里山口县宇都市也有,叫作“寒渍”。其制法是把萝卜盐腌了晒干,用木捶打了再晒,打了再晒,等到扁平了装入瓶内贮藏。从前据说是用草席包了用脚踏的,其制品可以保存几年,在新的时候作浅茶褐色,日子多了渐渐变黑,软而且甜。这样制法与壹渍稍稍有不同,其归趋则一,是传来的萨摩制法呢,还是别有所本呢,未能详知,但这也是一种菜脯。我平常很喜欢吃,常常从内人的乡里或是亲戚那里送了来,三十余年未曾断过,这是寒厨的珍味,吃饭下酒以及佐茶都常爰吃。年数浅的拿来切了,酱油加上酒或是凉开水制成一种汁蘸了来吃,咬去松脆,是酒肴的妙品。年月多了变成漆黑柔软甜美的,就是那么切了,也是佐茶的奇品,足以供利休的党人吃一惊吧。这里且将我“自家做的酱”(俗语自己夸说自家做的酱),来做这腌菜谱的结束吧。
载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至二十三日香港《新晚报》,署槐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