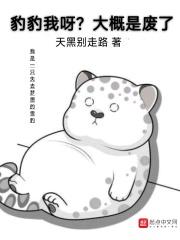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丞相大人最宠妻免费阅读 > 第70章(第1页)
第70章(第1页)
>
宁恪坐在床沿上摸了摸她的额头,还是没有退烧,反而比早上更烫了,倒难为她病成这样了还有精力折腾自己。
“我方才去钱记药铺给你买药了,不用太担心,不过受了寒而已,喝几天药,在床上休息几天也就没事了。想吃什么我给你买,想喝什么我给你熬……”说着说着,宁恪忽然住了嘴,呃,他不会熬汤。
为什么自己的话突然变多了呢,他沉思了一会儿,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宋吵吵者变话唠吗?
在他口中听到钱记药铺几个字……宋吵吵顿时想到了之前给他买的那包壮阳药,脸一黑,只想了一会儿,心里又是一叹,时间过去的真快,那个时候,她还是想尽办法逃离相府的宋家二小姐,命运真是阴差阳错,让她遇上了这么一个对她好的男人。
“那我要喝小米粥……”她恃宠而骄的哼唧道。
宁恪开始后悔自己说的话,有些赧色道:“没煮过……”
“哦。”宋吵吵很体贴道,“那你给我煮大米粥吧。”
“……”宁恪突然很想将她那张红扑扑的小脸捏成各种形状,斜睨了她一眼就去给她煮粥熬药了。
他不过出去一趟,买的东西倒很齐全,还扛了一小袋子米回来。也不知道以他的风度,是是怎么拎着两床被子招摇过市的……啊,想想就很可怕。
宁恪取了刚买的药起身进了厨房,将那药草细细的碾碎了,加了水,放在砂罐中熬了起来。刚过了一会儿,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苦涩的味道,像是浓稠岁月里那最难熬的滋味。
他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表情,只专心的注意着火候,心情如同那药味一般苦涩。他去买东西之前,还去了找过一个人。丞相长史杜奉曾是自己最得力的手下,一路将他提拔上来,即使没有感情也有知遇之恩,是自己难少有的信任之人。
杜奉倒不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见了他还如同以往一般尊敬,似乎忘记了眼前这个人已经被罢官了。他将朝堂中发生的事情尽数告诉了自己,旁的不说,就说这丞相职位,也不知皇帝是怎么想的,竟只是由御史大夫张同旭代领丞相一职,并未直接封官。杜奉明里暗里都在说,皇帝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人顶替,要是您攒一把劲儿,指不定还能归位呢!
宁恪倒没有想那么远,面对杜奉的话语,只一笑了事。
圣旨上那白纸黑字都是皇帝金口玉言,没有哪一条写着不准他再朝为官,也不知是皇帝故意给自己留的后路,还是不小心给漏掉了,但是无论如何,圣旨已下,再想改,也得问问谏官同不同意。
三年一次的科举就在明年了,秋季举行乡试,后年才轮的上春闱。罢他的官,抄的他家,都没有关系,他没有任何意见。凭他的才学,大可以从头再来,一步又一步的来。
大不了便将他那些官路再走一遍罢了。
时间还长,他不着急,有吵吵陪着自己走这段路,他一点也不着急。
眼下最重要的是先解决生计问题,之前留下的那点银子,也不知道能撑多久。还是得找个法子先赚到钱才行,他答应过吵吵不会让她受苦,就一定不会。
且说今日见到杜奉的时候,对方就死活要塞银子给他,宁恪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很温和,骨子里却是极傲的。让他拿别人施舍的钱,不异于在自己脖子上抹一刀。他之前不让吵吵跟着自己,无非就是因为郡主府能过好日子,再不济,她娘家也有自己刚送出的聘礼,吃穿自然是不愁的,无论如何也比跟着自己要过的好。所以,这一年,他至少要让她吃穿不愁才行……
似乎想的有些太多了,时间一长,药都煎好了,宁恪回过神来,将药盛在了碗里,还格外心细的给她加了点冰糖。
端着那碗药去了房间,刚一进门,那药味就弥漫了整个屋子。宋吵吵委屈的皱起了眉,又将自己埋在被子里,表示她看不到那药所以不用喝。
跟宋吵吵在一起呆久了,宁恪觉得他对掀被子这种事情已经练到一种境界了,什么时候搞一个花式掀被子比赛,他一定能拿魁首。
宋吵吵被他拽了出来,呼呼喘着气,两个人大眼瞪大眼。
“喝药。”直截了当。
“你不是说给我熬大米粥去了吗,你骗人!我要吃大米粥我不喝这么苦的药!”胡搅蛮缠。
“不喝?”宁恪扬眉,“要么回你的郡主府喝大米粥,要么在我这破屋子里喝药,自己选。”
话刚落音,宋吵吵突然坐了起来,伸手夺过了他的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生怕她不喝药,下一秒就会被丢出门外去似的,那可怜兮兮的样子让宁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宋吵吵皱着眉毛将那药朝嘴里灌,努力强迫自己喝下去,可是那味道实在太苦,本就因为生病而酡红的脸越发的红了。刚要接着喝,却被宁恪轻轻伸手拿了回去,柔声道:“我喂你吧。”
宁恪其实一直都不是很会照顾人,给她喂药的姿势也显得很生疏,偶尔还将汤汁洒了出来,弄的宋吵吵下巴上都是黑汁,看起来怪渗人的……宁恪起了玩笑之心,似乎还觉得她这个样子挺好玩,故意将药汁洒的她满脸都是,黑乎乎的宋吵吵一脸迷茫的看着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被人欺负了……
闹够了,宁恪拿了毛巾给她擦干净了,似乎觉得自己这种打一巴掌再给个枣子的做法实在不好,心下反省了一会儿,忍不住又给她擦了一遍……
雪在昨天夜里就停了,不过地上还有一层厚厚的积雪,窗缝里透出的风倒不是很大,却也“唔唔”的吹着,不过跟昨日比起来倒是好多了,还出了点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