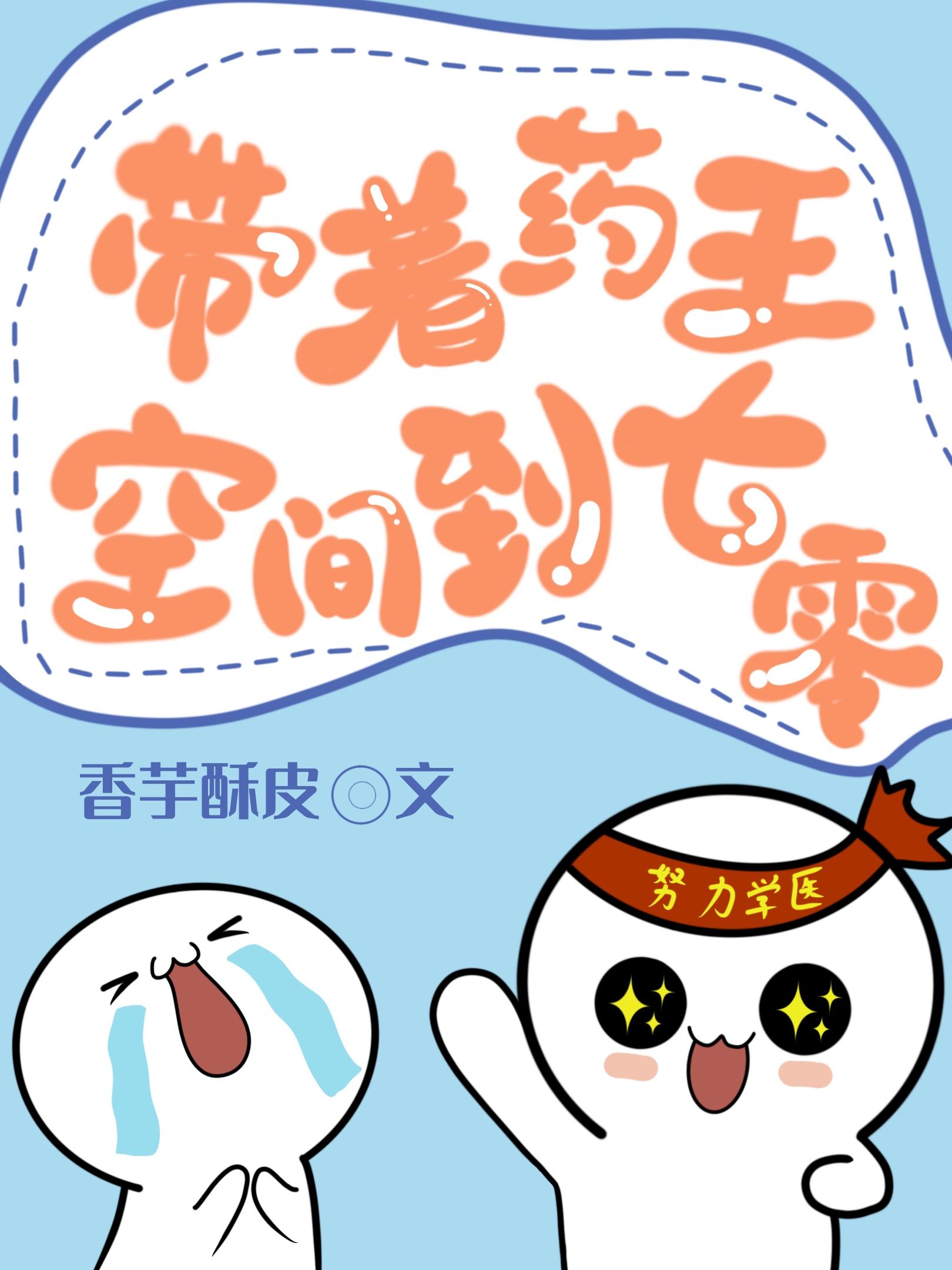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青灵按压痛说明什么 > 05(第2页)
05(第2页)
第一次抽烟,应该也是在十年多前。那时还青涩,并无太多人生的感触。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时间就是圆环,我绕了一大圈,又回到。
什麽都没有变,过去我在宿舍门外为梦箐和那个男人驻立,现在我在办公室裡为梦箐和这个男人驻立。
都是像这般点燃了一隻烟。
我看过一些网文小说,原还真以为自己会像妻子所言的那般——感到兴奋、刺激、或悲喜交加,想像着污秽和苟且的画面,然后打手枪。但真实的这一刻,我的心坎裡却是空空的。确实是有那麽一处地方,就像割开的伤口,一碰就痛得要死,但假如不睬它,也只是闷闷的,并不是不能共同生存。
所以我真实的心情,反而是空空如也的。
我木然地数着手錶的指标一点点跳动,不让思绪在任何心事上停留。
偶尔脑海中浮起荒唐,我都望向别处,它们失去了关注,便自然又沉下去。
这番迴圈了几番,再瞧见自己的伤心,便也像看他人的伤心一般平静了。
我被一口烟呛到,乾咳了几声。早知如此,不听父母之命才是对的。
那时的梦箐为了断我对这门婚事的念想,除了让我守门望风,更特地指使我去买那些用品。我人生的第一包烟,就是随着避孕套一起买的。
避孕套!!?
我身子一震,燃着的烟头几乎掉到身上。
因为不育的缘故,我们家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准备套套了,不光是我,连梦箐都澹掉了这个概念。至于严凯会不会自备,我几乎没有把握。而且,没有男人会随身带整盒套套,我慌张起来。
我拨打妻子的手机,无人接听,又打给严凯,竟也不通。看过手錶,这已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这更让我如坠雷击。我飞一般勐冲下楼,在便利店抓起一盒冈本,就打车往家裡急奔。
这般折腾,便又过去了半个钟头。
终于站在家门口时,我已大汗淋漓,双手也抖个不停,摸出钥匙好容易插入孔中,却现已被反锁。原来梦箐迎情夫入门后,便合上了外门的铁销。我一阵耳鸣,竟觉得几分旋天转地。
我杵着愣了好一会儿,才又想到可以敲门的办法,这时已顾不上惊动左邻右舍了,我咬咬牙,忙不迭地勐拍起来,砰砰砰。
几分钟之后,裡门开了,是梦箐。隔着铁门的她满脸惊讶,她犹疑地问道:“老公,你……怎麽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这才喘匀了呼吸,我把冈本从铁栏间递了过去,:“我怕家裡没有这个,我……”
“哎呀,我还真的忘买了。”隔着铁栅门,她转头大声问向屋内,“小严,你今天带了套套来麽?”,我双耳顿时臊得烫,我急忙朝妻子比了个嘘声的手势,这番对白让邻居听去了可不得了。
“老公,你真好。”梦箐吐了吐舌头,她鲜豔的唇,很润。
妻子正穿着一件圆领的短体恤,乳峰豆蔻隐约可见,露出平坦的腹部和肚脐,而下身仅着了条内裤,阴阜那儿鼓鼓的,十分诱人。而那一双长腿美若玉藕,白淨的足趾耀得人目炫神恍,我又心疼起来。
“你们……做了?”我悄声问道,她身上的洗髮水香味澹澹地飘了过来,这湿气未干的头髮,是事后的清洗麽?
“还……没呢……刚洗完澡。”妻子的脸羞得通红,她这时的神情就像初嫁的新娘,娇俏无比,但就是没有要开铁门的意思。
我并不信她的说辞,我试图揣度她的表情和衣着,离严凯上门至少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他们不可能什麽都没做。
这时躲在裡屋的严凯也闻声走了过来,他也是一副刚出浴的打扮,只见他脚上穿着我的浴鞋,一条毛巾横裹在他结实的腰上,我的眼睛难免不瞟了一眼他双腿之间的隆起。
看到是我,他也很是惊讶,忙哈腰做了个礼,并尴尴尬尬地喊了我一声陈大哥。
我老婆转头朝他问道:“你果真没带套套来,对吧?”
严凯瞧了瞧她,又看了看我,呵呵傻笑起来,真不知是真忘记还是假无心。
“哼,还好我老公有准备。”她扬扬手中的冈本,莞尔一笑。
梦箐拉着严凯的手,走进屋内。带上大门之前,她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老公,你走吧,今晚不要回来!”
当门合上后,我心裡的感受又和在办公室抽烟那会儿不同了,那一会我就像在看别人的幻灯片。而现在,我是真的心疼了。妻子伸手去牵严凯,那指尖是如何触碰到他肌肤的,光是这个画面,都像慢镜头一般将我大力撕开。
我一步一步踱步下楼,又慢慢走出社区。是路人投来的眼神,我才摸了摸脸颊,原来是在流泪。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坐在一个花坛那儿呆,一盒烟抽得只剩最后一根了。我正琢磨着要不要再去便利店买一包,这时电话忽然响了,我低头一瞅,竟是梦箐的号码。
我迟疑了一刻,还是按通了电话。
“怎麽……了?”
电话的那头却无人作答,只是一阵阵传来妻子的呻吟声,起先是零零落落的,逐渐越来越肆意连贯大声。再后来,我已能清晰听见床脚摩擦地板的吱呀声,以及男女私处撞击时那独有的啪啪脆响。
我明白,此刻,妻子的体内已经被严凯所进入了。电话内那端激烈的动静,恰是他在梦箐身上洩性欲的迴响。
此时我的内心,除了心痛,更有了一些难以言说的感受。我没办法解释自己,也从未认识过这样的自己,妻子正被人侵犯,而我的下体却不争气地充血涨硬了起来。
电话那头,妻子快丢的时候,竟喊起我的名字:“我就要给他了,啊我是严凯的人了!我要飞了,要死了,再深点……老公,你听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