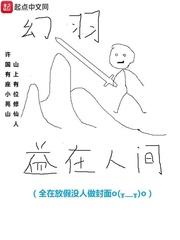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歌曲吹灭小山河 > 第238章 脊背不弯(第2页)
第238章 脊背不弯(第2页)
丁叔气地拍了他一巴掌:“你用你的脑子想一想,小辉能孤注一掷护着你出来,那是因为他潜伏在里面,足够了解那个地方,你呢,你用你的脑子想一想啊,你孤注一掷,你连那地方有几道门你都不知道,还没开始跑就嗝屁了!”
张金国压抑地哭着,心头哽着一口气,别人再怎么说,他都无法说服自己。
那是两条活生生的生命,却受尽屈辱死在他面前。
那个孩子还没有机会穿上他为之奋斗和热的警服,他甚至连警号都还没来及拥有,却怀着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导致父亲遇害的悲痛离开这个人世。
而他的搭档,在那屈辱的二十多个小时里,他受尽了这世上所有的酷刑,却无时无刻保持着清醒。
他在那样的折磨下,依旧咬牙切齿地教导他的孩子:“儿子,好了,咱当警察的,一辈子都得顶天立地!你爹,钢做的!”
张金国重重地搓了一把脸,擦了自己的眼泪,他抬起头:“老丁,我现在想想,当初不是我命大逃了出去,而是对方,他就像是玩一场游戏一样,故意放我离开。”
丁叔脑子转了几遍,他背着手在地上走了几圈:“什么意思?你说,是对方故意的?”
张金国站了起来:“是!这就是他们的狂妄之处,他们把人命当儿戏,他们以玩弄我们警察为乐趣,他们放我走,直到如今又找到我旧事重提,是因为这场游戏,他们想开始就开始,想结束就结束!”
他也如同丁叔一样,无视了自己那双残腿的疼痛反复地走了几圈。
“凭什么!我不服,我不会再让他们那么嚣张地耀武扬威!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警察的骨头,是钢筋做的,不是任由他们揉捏的!”
“好!”丁叔怒喝一声:“老张,就冲你这句话,我帮你!”
“我就知道。”张金国红着眼:“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丁叔一脚踢在了他腿上。
与此同时,骆寻他们在屠国林家的地下室,找到了一箱肥皂刻的猫。
“屠国安的好就是用肥皂刻猫。”
骆寻着那一箱神态各异的猫:“迟夏,你觉得这是谁的手笔?”
迟夏在一箱子猫里面挑挑拣拣,最终找出一个:“至少这个,不是屠国安刻的。”
“嗯?”曹斌好奇道:“迟夏,你咋出来的?这都差不多啊?”
“忽略掉雕刻线条和手法等专业性的问题,雕刻这只小猫的肥皂,是两年前出的新款。”
迟夏闻了闻:“这个味道,的确是新出来的,而屠国安五年前就被抓进去了。”
“那咱们把这箱子猫带回去,让人鉴定一下呗。”
卷毛说:“就像纹身师一样,虽然是同样的图案,但每个纹身师都有自己走线的方向和习惯,这个道理放在雕刻上也是一样的吧?”
“我说你个小卷毛,该聪明的时候你是一次都不落啊。”
曹斌杵了卷毛一下:“你最好保持你这种聪慧,直到咱们迟夏办完这个案子,要不我是真担心你给迟夏拖后腿啊。”
卷毛笑的憨憨,两指并在一起在空中画了几个圈,然后一点脑袋:“你放心,我已经跟它传达过你的意见了。”
曹斌顺着他的话:“他怎么说的?”
卷毛说:“他说得令!”
两人说话间,曹斌拿起犄角旮旯里的一包东西:“哎,有点怪啊……”
“怎么?”大家的目光都被他吸引了过来。
“以这个地下室的灰尘来,平时基本没人来这个地方,屠国林也没让人来打扫,但是你们这份刻刀,有点过于干净了吧。”
他把东西给迟夏递过去:“着像是刚放进来的不久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