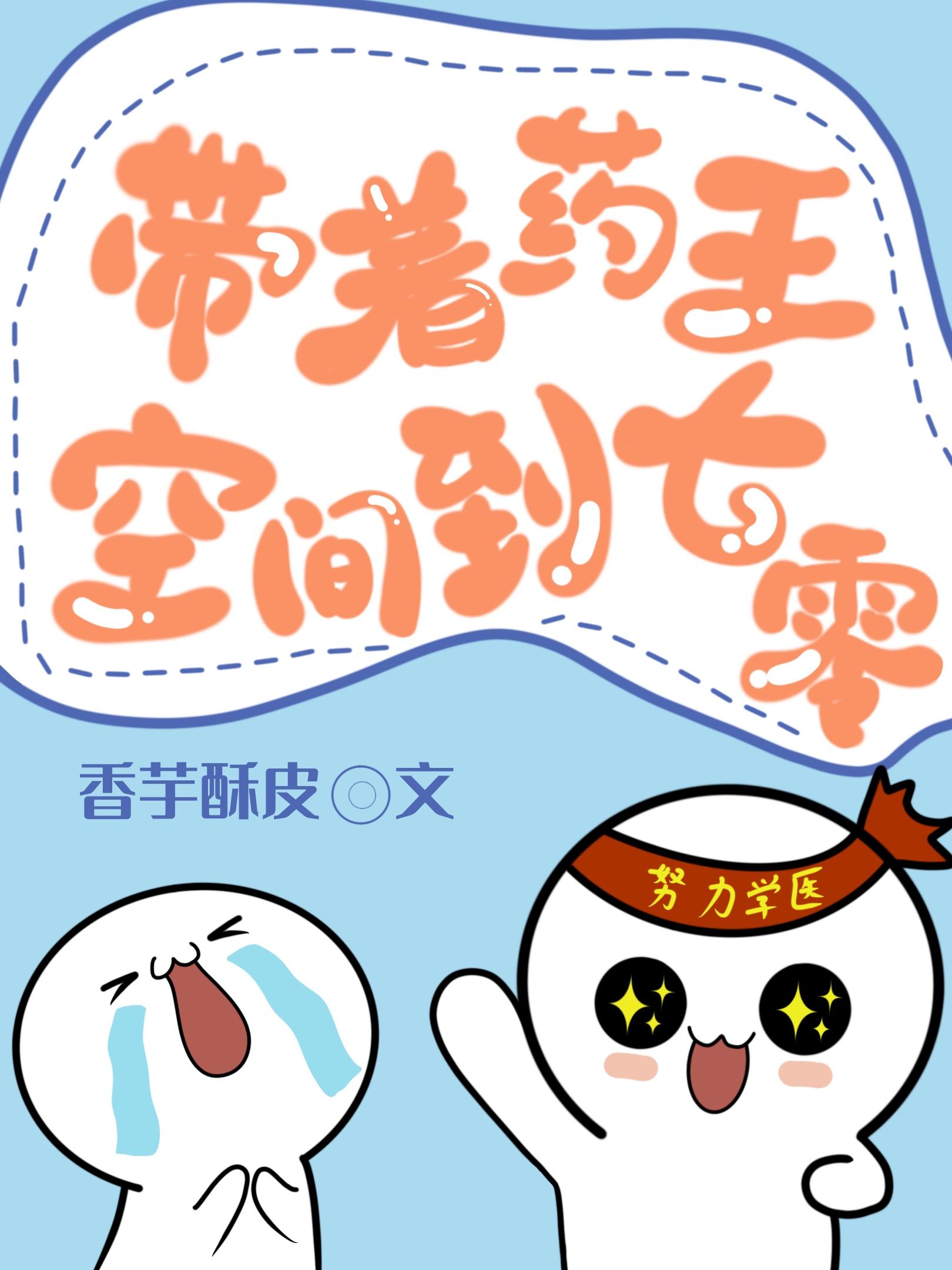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余污人物关系图谱 > 155阿莲遇刺(第1页)
155阿莲遇刺(第1页)
营帐里又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墨熄走到榻前,在顾茫身边坐下,抬手摸了摸顾茫的额头触手仍有些偏烫,但终归比前几日好许多了。
“梦泽说你白日的时候醒来过,但许是我运气不好,每次来瞧你的时候,你都昏睡着。”墨熄低低地对他说,像是希望他听到,又像是希望不搅扰到他。
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挚时,无论平素有多强大,都是软弱的。
“血魔兽的残魂已经被重新封印起来了,封存得很周全,你又一次完成了你的任务。”墨熄轻声道,“你啊,无论旁人给你的任务有多难,要求有多苛严,你总是能够完成的。君上从来就没有错你你比谁都更能成事。”
他低下头,额头轻抵着顾茫的前额。
“只是你什么时候才能多关心自己一些呢。”
躺在榻上的人安安静静的,柔长的睫毛在眼睑处垂落浓深的影。
墨熄低声道“明明知道自己身上的黑魔之息已经压不住了,却还是要解封妖狼之血,就为了拖住国师,让慕容怜能有时间把锦囊交到我手里。”他闭上眼睛,眼珠在薄薄的眼帘子之下不安地动着。
“师兄”
睡熟的人并没有任何的回应。墨熄就这样与他额头相贴,良久之后说“所有能做的事情你都做完了,等我们回到都城,你就好好养病。什么都不用再忧心,一切都有我。”
“”
“我不知道我能护你多久,但只要我还在一天,就不会教任何人欺负你。”
“”
“你安心休息吧。”
墨熄说完之后,又陪他坐了好一会儿,待到有传令官急报城东灾民安置情况,他才起身离开了帐篷。
外头的风刮得湍急,帐帘一掀,带起猎猎风声,一落,帐内又复归阒静。
在这无声的静谧中,躺在床榻上的人睫毛轻颤,泪水顺着柔软的脸颊淌落到鬓发深处去顾茫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着,每一天晚上墨熄来他的时候,他都是清醒的。
只是不知如何自宽,怎样面对。
他不畏天不畏地,唯独畏别离。
那一天他自解封印,激发体内所有的妖狼之血与国师对战,自此之后黑魔之气就在他体内信马由缰失了控,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记忆几乎是崩塌似的地在流逝,而这种流逝是无论如何遮掩也遮掩不了的。
而墨熄已经这样万事缠身了,如果每天来他的时候,都发现他的头脑比前一天更不清醒,墨熄会怎么样
快刀枭首固然可怕,但钝刀子一寸一寸地割肉更让人煎熬,顾茫不希望将墨熄拽入这煎熬之中,于是他宁愿选择不与墨熄直接地交谈。
只是当夜深人静,大帐无人时,他会从枕褥深处摸索出之前写下的回忆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抚平,犹如溺水之人捉住浮木,近乎偏执地一遍一遍细。
那上面写着的内容初时还能努力想起,但是一天过去,又一天过去,纸上的字就越来越像别人的故事,到了今天,他几乎已半卷都无法回忆出任何的细枝末节了。
顾茫抬起手,将那因翻阅太多而皱巴巴的纸页揣在心口。他是那么用力,以至于手背处经络浮起,将回忆集摁在怀中,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分崩离析的记忆都锁回心底。
他蜷在床上,终究是一夜未眠。
重整战后的大泽城耗了七日。
到了第七日晚上,大军诸事抵定,准备拔营班师。而到这个时候,顾茫因为时光镜而闪回的记忆,已经所剩无几。但这还不算最糟的,记忆就算缺失,再怎么说人也至少能像前往蝙蝠岛前一样,最恶劣的是因为黑魔之息不受控制了,所以顾茫的精神随时随刻都面临着崩溃暴走。
梦泽每天都必须给他服下安神宁心的药,才能勉强压制住他的邪气。
这一天晚上也不例外,顾茫照例喝完了梦泽送来的药,而后坐在床沿,一边默默玩着手指,一边想着明天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墨熄。
他总不能一直装睡。
正在他想得出神时,忽听得外头有近卫道“公主,望舒君求见。”
梦泽正在收拾汤药,闻言一怔,和顾茫对视一眼。
顾茫微感诧异“他怎么来了”
“不知道,但你先戴上覆面吧。”梦泽说着,将面罩递给他。
尽管军中修士现在大多笃信了这个神秘的“近卫”就是顾茫,此事已然是昭然若揭,但再怎么样,揭开和没揭开也不是一码子事。最起码的窗户纸还是需要的。
顾茫刚刚戴好覆面,慕容怜便金刀大马地进来了。
一进屋,桃花眼先扫过顾茫,而后才落到了梦泽身上。梦泽将最后一包药粉放入药匣子当中,转头对慕容怜微笑道“怜哥,明早就拔营回朝了,你不去早些歇息养足精神,来这里找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