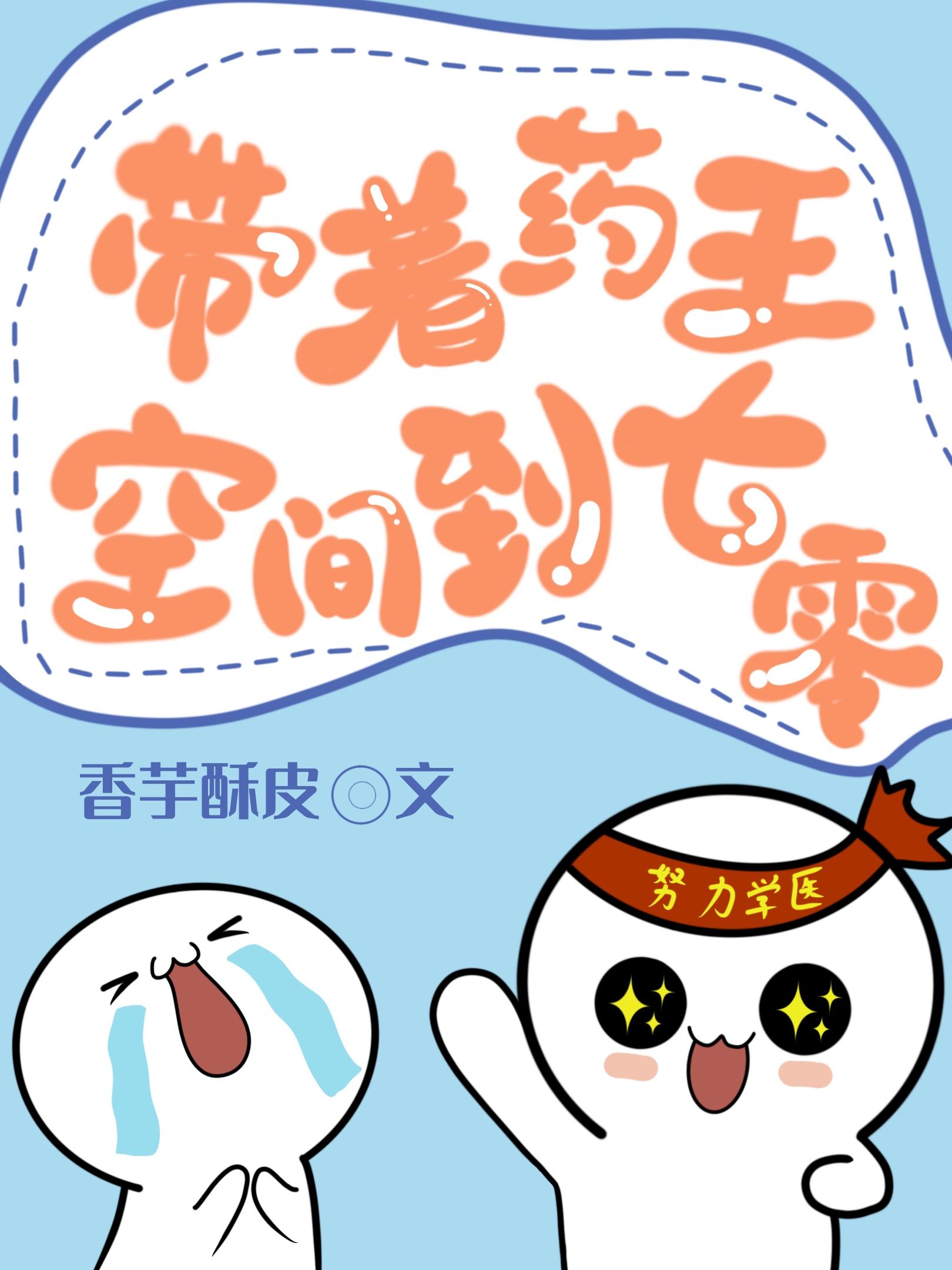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大宋泼皮 最新章节无弹窗 > 0126两面下注二合一(第2页)
0126两面下注二合一(第2页)
刘锜骑在马上,故意落在后面,找聂东搭话。
他觉得聂东此人只是个军中粗汉,没甚心眼,想来三两句便能套出话来。
这一幕被朱吉看在眼里,想笑又不敢笑,憋的脸都红了,肩膀一阵阵抖动。
这傻小子!
刘锜拱手道:“这位将士如何称呼?”
“某家名唤聂东。”
聂东挑了挑眉,眼中闪过一丝戏谑。
“聂大哥以前应是禁军罢?”
方才吃粥时,借着篝火的映照,他便发现聂东等少数骑兵脸上俱都有刺字。
虽看不清刺的是什么字,但刺字的位置、颜料以及手艺,乃是禁军中的手法。
聂东答道:“某家原是小种相公门下。”
西军?
刘锜心里顿感亲近,好奇道:“既是三种门下,怎会在此?”
聂东愤愤不平道:“还不都是童贯那个奸贼,纵容贪官污吏抢夺我等战功,克扣军饷赏钱。轻敌冒进,导致西军大败。”
“童贯这个狗贼当真是该死!”
刘锜一拳砸在腿上,义愤填膺的附和道。
他父亲便曾被童贯抢夺过军功,如今又被针对打压。
聂东趁热打铁道:“刘相公的威名,某家也有所耳闻,心中敬佩的很。据说收复河湟,劝降吐蕃本该是刘相公的功劳,结果却被童贯这狗贼抢了去。”
“嘿!”
说起这个,刘锜更加来气,怒道:“东京城里的皇帝也是昏庸至极,明知童贯抢了我父军功,竟还如此纵容这个阉狗。”
三言两语间,两人便同仇敌忾,变得亲近起来。
聂东也在不知不觉间,掌握了主动,问道:“小衙内不在边军,怎地来了山东?”
刘锜丝毫没有察觉,反而大吐苦水:“我父遭童贯打压排挤,担心连累我等,便将俺送来舅父身边,弃武从文,读书科举。”
“小衙内有名将之资,若是不做将军,太浪费了。”聂东吹捧了一句。
“着哇!”
刘锜心中大喜,激动道:“俺也是这般觉得,念个劳什子书,上阵杀敌,保家卫国方为好男儿。”
一路闲聊下来,他已将聂东引为知己,不过好在他也没忘了目的。
瞥了眼队伍最前方的韩桢,刘锜压低声音道:“聂大哥方才说所道法秘术,可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聂东点了点头。
刘锜赶忙问道:“有何神异之处?”
聂东添油加醋道:“此法若练至大成,举手投足间,便能催动全身气力。小衙内天赋异禀,虽比之县长差了一些,但也是人中龙凤,若是能学成,以一当百,不在话下!”
“当真?”
刘锜又惊又喜,音调不由抬高。
“某家从不诓人。”
聂东拍着胸膛保证,配上一脸憨厚的表情,让刘锜不疑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