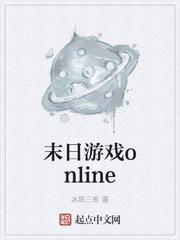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克拉夫特言论 > 第二十八章 今日无事(第2页)
第二十八章 今日无事(第2页)
结束教学后,大家欢乐地到学院旁的酒馆去解决午餐,依旧是经典的烤鱼,配上一些莴苣、洋葱和豆类。
卡尔曼教授所言非虚,这家酒馆在学生中极受欢迎。唯一的美中不足是其他学院的学生也在场,大家就不能畅所欲言地谈论可能会引起误会的学术问题。
午餐散场后,克拉夫特会去教授的房间午睡。讲师在学院里是没有专门办公室的,不过卢修斯很乐意向他暂时开放教授的地盘,同时每天在这里为卢修斯简单做个检查。
结果自然是没有任何异常。在远离黑液以及相关物品后,卢修斯对进行实验的兴趣似乎都有所减少,不再频繁地提到黑液,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午睡后,克拉夫特会开始每天的抄写工作。
主要内容是那些暂时毫无卵用的专业知识。在考虑后,克拉夫特还是决定把自己所学过的一切记录到纸面上,封存起来。
就算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那一天,也能捐献给有保存能力的大学或者别的什么机构,静待技术水平发展到足够使用它。
自己可以写很多份,总有一部分会在历史中被保留下来。到时候,这个世界的医学发发展能少很多弯路,少牺牲很多人。
为此,他从祖父给他置办房产的钱里挪用了一部分出来,自费购买了质量更好的纸和墨水。
克拉夫特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花体和哥特,摒弃了一切修饰和连笔,用最死板、清晰的字体开始一字一句抄写。
();() 这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尽管他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所学的每一本教材,但翻译的本地化工作依旧让他的进展速度堪忧。
这项工作的目的是把信息尽可能精准传递给很多年后的人,不能原封不动地使用当代的一些语意含糊词汇,不允许太多的音译,要求根据本地词汇词缀进行造词。
所有专有名词在第一次出现时,必须进行解释,但解释中又有其他的专有名词,顺势扯出了更多的概念和引用。这对一个过目不忘的大脑升级人来说也是种巨大的折磨。
然而克拉夫特在诺斯语的使用上水平不高,还得拜托卢修斯从文史学院那边借来专业的词典,自学构词规律和排除拼写重复。
接着他就发现这本几经周折借来的、号称最全的词典,本身里面就有矛盾错误之处。
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直接导致了克拉夫特的进度不到刚动笔时预期十分之一,至今他还困在大一《系统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的前几章里不可自拔。
这还是因为他备课内容是跟抄写内容有所重叠,节省了不少时间,不然他估计还在翻词典。
再想到后面还有几百上千万字的书等他去逐字逐句翻译和配图,这种崩溃感成功击垮了这个异态现象都没有干掉的男人。
在下午两点的钟声敲响时,克拉夫特从桌上爬起来,拿出纸笔开始今日的抄录。
写满字迹的手稿在旁边摊开晾干墨水,阳光穿过窗户撒在满桌纸张上,墨水瓶子的影子随时间偏移拉长,外面偶有学生们的交谈声传来。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恍惚间似乎穿越从未发生过,一心学业的灵魂正坐在下午的示教室里,面前是刚做完的笔记,不小心用手抹到就会糊成一片。
书写让他有种忘我的感觉,直到光线昏暗,从这种状态里惊醒过来,钟楼已经完成了下午的第六次鸣响。
克拉夫特起身收拾东西,将一天的成果叠放整齐,独自夹着书回到旅馆,独自享用鳕鱼浓汤和面包,再独自回到房间点亮蜡烛。
摊开质量不太好的脆纸,这种纸被用于不那么重要的日常记录,用粗糙的纤维压制而成,时间太长的话会像波力海苔一样咔嚓一声折断。
不过用在这里正好。他要在困倦前为明天的课程写好教案,在脆纸上勾勒出要画的草图。
晚上最后一次鸣钟后,为了保证明天的精力,克拉夫特吹熄蜡烛,结束他重复而充实的一天。
这样就很好了,克拉夫特躺在床上,在黑暗中久违地感到了安宁。他愿意就那么度过一生,从讲师到教授,有可能的话闻名四方,传书后世。
至于什么黑液,什么异态现象,最好永远永远别去碰。等卡尔曼教授回来,告诫他离那玩意远点,来帮自己编书不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