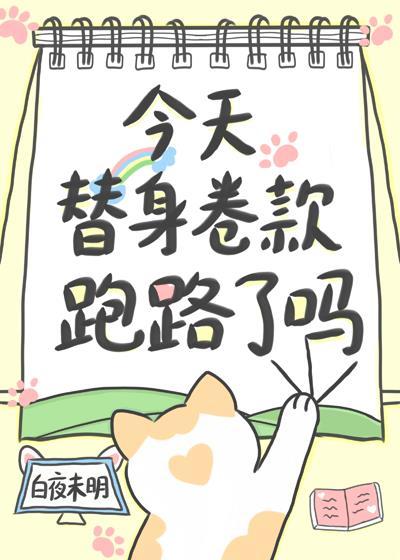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清明祝什么 > 第十三章 请符舍命一(第2页)
第十三章 请符舍命一(第2页)
“廷龙你来此何干?”
“都督还记得之前的仇呢?”叶永甲没回答,反笑着问他。
“哪有什么仇呀……”赵授口上虽这般说,脸色却不好看。
“赵都督,之前的事是我糊涂了,在下道歉;您看我这番来,不就是要戴罪立功么。”
“怎么立功?说来听听。”
“您可知道虎符的事儿?”
“知道,可与我没干系,”赵授重叹了口气,“我这都督一不能做主,二不能领兵,那虎符也不在我手上。”
“您不会向卢大人要去?”
“不敢哪!”
“不如都督写个呈子,由在下递过去,我再劝劝卢大人,说不定就成了。”
赵授警惕地看着他:“怕你到时候在卢大人面前说坏话……”
“绝无此事,”叶永甲试着向他解释,“您想,您是卢大人的什么亲戚?”
“你不知道?问我?”赵授的口气并不和善。
“在下说错了……您继续听我说,您是卢大人的表兄弟,且受他屡次关照;在下与知府大人非亲非故,哪轮的到我进谗言?赵都督有何不放心呢?”
赵授深觉有理,再加求符心切,便一口答应了:“我这就写呈子;可你若办不好,别想在淮宁城里呆了!”
“是,是……”叶永甲说话谦卑,生怕得罪了他。
赵授在厅里写了呈,交到叶永甲手里,他遂离开此地,走到知府衙门,听说卢德光在书房休息,便不去拜谒他;转而问了黎用的去处,将呈子递到他那里,说是赵授托他来的。
叶永甲如此做的缘故是因自己威信渐失,递进呈子去又轮不上他说话,故令一个知府的梯己帮着送过去,卢德光信得过黎用,自然将此信当真,进而引起猜忌。
卢德光果然犯了狐疑。他用手掐着这封呈子,半天没说话。
“奴才以为……”
“不用你说,”卢德光开口了,“我看这赵授也是有些问题。”
“这信是叶永甲给我的,恐怕……”
“不是,”卢德光摇摇头,“他要真想引我猜忌赵授,直接送过来,在我面前进几句谗言,岂不更省便?何故交你手上……这定是赵授指派的。”
黎用闭口不答。
“他好大的胆子!”黎用在旁明显感到了卢德光喉咙的震动,“难道没人告诉他,这兵权是我的吗!”卢知府一甩手,将那封呈子‘啪’地扔到桌上。
“还有那几天,我前脚派了他去联络钟知府,后脚监察御史便来了,今日又闹出这种事……你说说他的嫌疑能不大吗!”
“那知府大人是何意见?”
“你明日就派人去都督厅给我搜查!……至于起兵,看来要歇一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