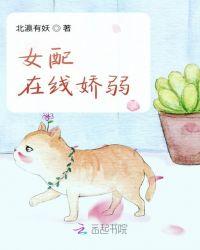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皖南牛二新书 > 第六十七章 争锋相对(第3页)
第六十七章 争锋相对(第3页)
他很清楚。秦墨所以种菜,做海底捞,弄酒,都了他。
他能力,保护好秦墨。
“滚开!”
李越一脚揣在那个手执棍东宫侍卫身上,反手又几个耳光,在按压秦墨脸上,“长东西,听见七姐命令?”
骂完,他连忙将秦墨搀起,看着秦墨脸汗,和他嘴上牙印,自责几乎将他吞,“事?”
秦墨龇牙咧嘴,“死!”
见秦墨能皮,李越松了口气。
“大胆,他们按孤旨意行事,李越,谁给你胆子动手?”
李新脸沉,“你知知道自己在做什?”
“知道!”
李越直接了去,“臣弟在帮太子纠错!”
李新怒急而笑,“纠错?哪错?”
“一件事,从头到尾,就个错误!”
李越昂着头,和李新对视,“秦憨子种出逆季节青菜,因想让父皇和母吃上新鲜蔬菜,皇宫每供奉,难道太子吃吗?
等孝心,便苍天知道了都会感动,又会降下天谴?”
众都一愣。
秦墨逆转四季,就了孝顺陛下和皇娘娘?
李玉漱看着李越,蹙着眉头,很快她便明白,李越在帮秦墨。
李新也哑口无言,那手软,吃嘴短,每天青菜,他吃最多!
也降下天谴。
“其,以新粮酿酒,更无稽谈,就算秦墨真用新粮酿酒,又会把证据留在现场。
秦墨只憨,傻,秦家也傻,所以一条,更荒谬至极!”
“其三,与民争利,在臣弟看,个民也完全民。
寒冬腊月,青菜金贵,一株青菜就要买到两银子,供应求,两三碗过岗,足足要五十两银子。
试问什民吃一顿饭能够吃几百两乃至上千两银子?又那个民能够像秦墨一样,在冬天种出青菜。
他们既然种出,又能说,秦墨与民争利?”
“其四,罪状说和秦墨结党营,天大笑话,世都知和秦墨关系匪浅,若要结党营,也一朝一夕了,而们三岁穿开时候就结党营了。
枉告可能理解朋友和结党营意思,若那懂,臣弟愿意当面解释!”
“其五,秦墨殴打陈知县,臣弟虽然在场,但陈知县捕风捉影,以下克上,犯了天大忌讳,要说,秦墨打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