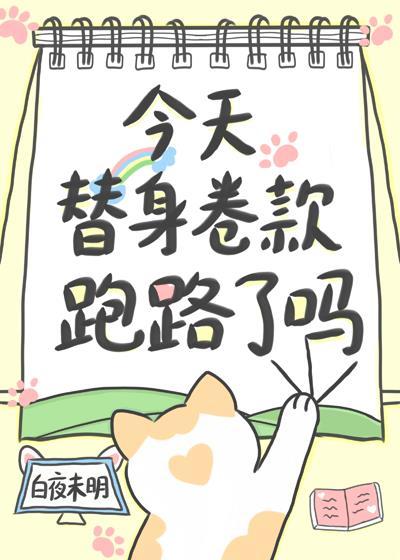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清明祝福说什么 > 第四十二章 重逢免府三(第2页)
第四十二章 重逢免府三(第2页)
较江都的暗潮涌动而言,仪征实在是安宁之地。吕家在这些不紧不慢的日子里渐渐恢复声威,不仅当铺又开了几处,小商人们亦都来依附。
吕正甫一点不关心外地的事情,他丧子之后,行事总有些迟缓,讲话费劲,耳朵更聋,故平日只问正事,懒与外人闲谈了。
今日他听说过家的人又来,便一字一顿地问:“还、还是过楚子?”
“过楚子?”禀告的奴才哈哈一笑,“那厮都死了几个月了!”
“死了……”吕正甫激动地咳嗽两声,家人搀扶住了。
“这番是谁来?他儿子?”
“那厮不得好死,又断了子孙,哪还有儿子。”
吕正甫流下两行泪水:“天道好还,终报寿儿之仇矣。报应,报应啊……”
“这回乃其胞弟接管了染坊,叫过湘人,说来此给主子您拜年。”
“过家没一个好东西,此来必有诈,不见。”吕正甫的目光充满了敌意。
“量那二十出头的毛孩子,有什么成见?”这奴才冷笑道,“主子,趁此之际,正摸清其底细,岂不是好事?”
吕正甫道:“那就按你说的,老朽不惧。立刻动身,前往迎迓。”
“吕老爷子!”过湘人跳下车来,向吕正甫一躬身。
吕正甫端详了他的相貌,笑道:“过掌柜,你兄长与我甚有情谊,可谓至交。今其既去,吾尚悲惜不忘,今见掌柜一表人才,如睹故人。”
湘人道:“吕老爷子待人如此恭敬,晚辈羞愧难当。”
“何必客气呢,”吕正甫笑道,“来,我们入府说话。”
“你家染坊想必生意兴隆吧?”吕正甫先问道。
“生意愈发好了。”湘人按部就班地回答。
“您的当铺恢复的还好吧?”湘人又问。
“相当不错。”正甫听了他这句话,气得牙痒痒。
“晚辈刚开始打理生意,不知这开当铺有什么规矩?”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开当铺嘛……”吕正甫刚想回答,忽然回过神似的,擦了擦眼睛:“过掌柜,你也……也要开当铺啊?”
“是啊,光一个染坊干的也没意思,”湘人仰头望天,“当帖都要拿下来了。”
吕正甫倒吸一口凉气,脸色瞬间惨白起来,苦笑道:“好,好哇。”
“您还没回答晚辈问的呢。”
吕正甫翻了两个白眼,手开始不停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