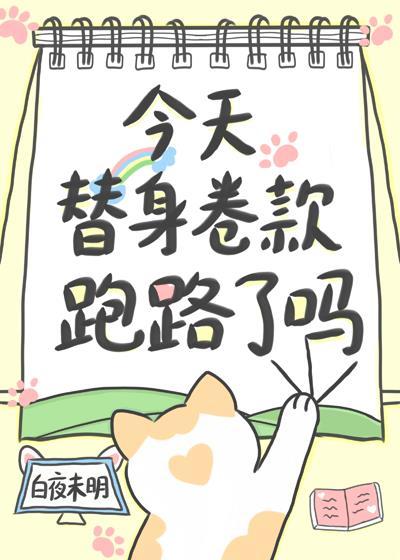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北马仙尊免费阅读 > 第36章 黄三姑(第1页)
第36章 黄三姑(第1页)
本眯着,美滋滋着烟黄三姑,脸上表一下就僵了。
一双眸子寒光暴闪瞪溜圆,一把抓了三衣领子;“你说什!”
面对她此刻副要吃模样,跪在地上一只耳和两个,吓得头都敢抬。
被她抓着三,对着她张脸,更吓得周身冒凉风,哆哆嗦嗦道:“太,,说六子让,让劈死了……”
黄三姑抓着他衣领手,猛一个掌甩出去,直接将三打翻在地。
三嚎叫一声,在地上打了滚,嘴里掉下两颗牙。
三捂着嘴跪扑在地,哭十分委屈:“太你,你打干什呀?”
黄三姑一脸伤悲,用手揉着心口,愤恨,用烟袋指着地上三兄弟:“家小六子今天,定让你们帮狐朋狗友给带坏了。
你们一个个成天一个正,把那小六子捧高高在上,下可好,他摔死了,难道你们该打嘛!你们六子命!”
下面跪着一只耳三,吓得连忙接着叩头,一只耳道;“家你可错怪们了,次那六子兄弟,一心向上,本想找一段好缘分,四海扬名。
想被那蟒金花拒门外,六子兄弟与他讲理,料蟒金花恃强凌弱,出手间一道寒雷,就将六子兄弟活生生劈死在们前。”
一只耳说到里,悲愤伤;“晚辈生,因大家都黄家一脉,看过去,带着两个兄弟挺身而出。
想到说过两句,那蟒金花就切了晚辈一只耳朵,家,事您可能怪罪给们,们可都被蟒家欺害,而无处申冤家。”
一只耳说到悲伤处,哭心酸无助,,三跪在地上也都委屈流泪。
黄三姑见一只耳,左耳确实被削掉,又将此事缘由说清清楚楚,如此大事,谁也敢胡编乱造让替。
黄三姑想着玄孙惨死他手,心如刀绞,悲痛难言,默默闭上睛,流下两行泪。
等她再睁开睛时候,双眸中像两团在烧;“蟒金花,蟒金花,难道真金花教主成?”
一只耳连忙道:“太,那蟒家女子,自然金花教主,她自称师承在碧游宫,被金花教主赐名。实在蛮横心狠,一点道理也讲呀。”
黄三姑脸上泪痕未干,&xeoo冷笑;“黄三姑,平生也说过少大话,但说大话,本唬什,凡事,要真本事下见真章!”
黄三姑,看向面前跪着一只耳三兄弟;“你们三个起说话。”
一只耳三兄弟起身,规矩实站在原地,委屈,显得无助又心虚。
黄三姑一脸肃正望着他们,训斥道;“作黄家生,一个个贼眉鼠,像什样子,修了几百年,竟一身皮毛相,简直成体统,一个个点骨气,杆子都给挺起!”
黄三姑站起身,掌中大烟袋一晃,另一只手里,握了一盘龙金柺。
此刻黄三姑双眸放光,威风凛凛;“别说个蟒金花,姑听说过,就算她真碧游宫教主门下,难道杀就偿命嘛?你三个就带去找她,到要见识见识。”
一只耳连忙话;“太,会蟒金花伤在身,早府休养多,现在只能找到胡小东。”
黄三姑微微皱眉;“胡小东?小六子本想与他结缘?”
一只耳点头道;“太,一点错,个胡小东今年才十岁,而且特别挑仙家,他仙家谁,都他自己说算。”
黄三姑听了话,双眸寒光电闪,突然放声狂笑;“哈哈哈!好,十岁,挑仙家?很好,姑倒要看看他什变!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