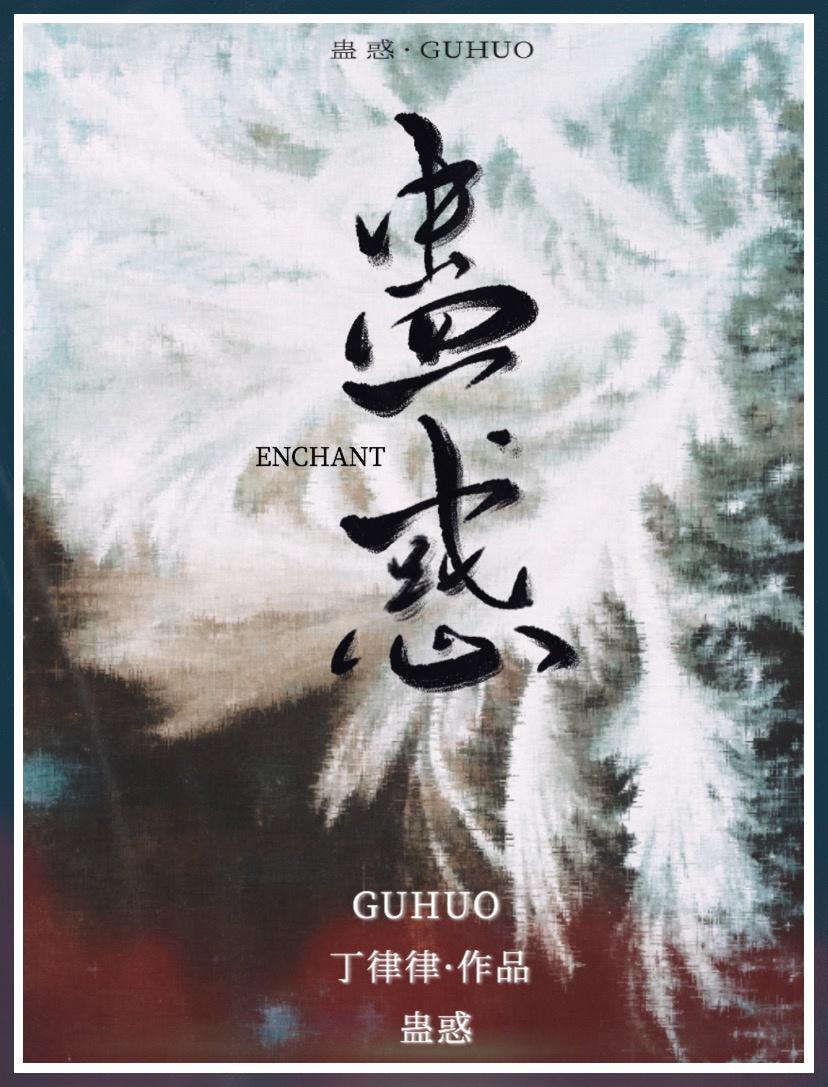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雨溺简介 > 第 97 章 肋骨(第3页)
第 97 章 肋骨(第3页)
喉结艰难滑动,陈泽野手臂紧紧箍着她肩胛,声音像是混了把粗粝的沙“安安。”
“会嫌弃我吗。”
每个字都透着他的不安与惶恐。
祁安眼泪掉得更多,像是断了线的珠子,带着滚烫的温度,一颗一颗滑落藏进他衣领里。
手攥成拳胡乱打在他身上,力度轻到可以忽略不计,祁安委委屈屈地憋出一句话“傻不傻啊。”
她怎么可能会嫌弃他。
他是全世界最好的陈泽野啊。
“忘记我之前说的话吗。”
哭腔越来越强烈,鼻酸将氧气悉数攫取,祁安用全身力气去抱他,让他感受到自己的真实存在“你被我赖上了,这辈子都逃不掉的。”
“别想推开我。”
陈泽野听到她的哭声,心软到不像话,也疼到不像话。
痛意由心脏生发,钻进身体里的每一寸,将神经剥脱敲碎,比任何一种上的疼都更加致命。
“不推开。
”他反反复复保证着,“我也离不开你。”
陈泽野把人抱起放到自己腿上,指腹蹭了蹭她的脸颊,大概是觉得不够,又凑过去吻着安抚很久。
脸上的泪痕被一点点吻干,可心脏还是疼到无法呼吸,自责的情绪紧接着生出,祁安埋头咬唇重复“都怪我。”
“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你就不会生病。”
当年那场闹剧宛若蝴蝶效应,一切都是因她而起。
“不是的。”
陈泽野打断她的胡思乱想“宝贝,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
“医生说过,我的病是因为原生家庭造成的。”
父亲多年来残忍暴戾,母亲的去世又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堕落与颓废从十一岁开始便扎根在他的血肉里,像是一双无形的手,试图将他摧毁,将他掏空,将他推到无尽的深渊中。
抽烟、酗酒、打架,他在这些恶习中放任自我,用消沉麻痹神经。
最狼狈最浑浑噩噩的那段时间,是祁安将他拉了出来。
潮湿阴暗的连雨天,雨水倾盆砸向地面,她踮起脚为他撑开雨伞,用与温暖驱散黑暗,让他见光的希望。
万物复苏,枯木逢春。
可他们还是分开了。
唯一的光也不见了。
“再后来我去了国外,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交流也不顺畅,身边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不适应,情绪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自己根本没法控制,过医生才知道,原来我是生病了。”
双相情感障碍很痛苦,时而亢奋急躁,有消耗不完的精力和快乐;时而却又压抑消沉,积极的情绪被从身体中剥脱,对任何事物都失去兴趣。
两种极端的情绪同住进身体,像两个凶狠的恶魔,他们斗争着也撕扯着,恨不能将他分成两部分。
但最痛苦的并不止这些。
他心的姑娘在大洋彼岸,与他隔着几万公里。
“不过”陈泽野掌心抚着她长发,眼眶像是浸透血色般泛红,不知是在对自己,还是在对祁安说,“别怕。”
“别怕啊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