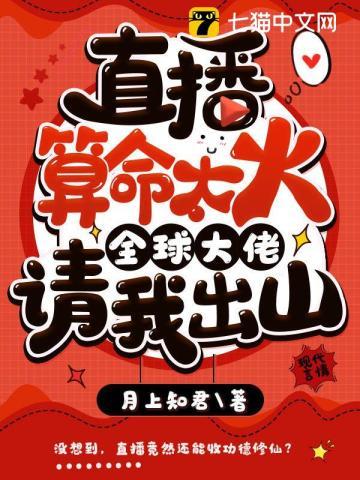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仵作医妃燕离 > 第122章 爱情1(第1页)
第122章 爱情1(第1页)
她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哀求侍卫。
左边的侍卫不耐烦地用剑鞘拨了拨她:“你也不看看天色多晚了!主子奶奶早歇下了!再说你这样儿的,也配来颜府做事?”
另一名侍卫笑了笑:“亏得提督大人走了,不然,不是叫他瞧了咱们颜府的笑话儿?”
妇人磕了个响头:“二位小哥儿,求求你们了,我……我所有盘缠都用光了,今晚没处落脚,你们帮我找个能拿主意的管事妈妈,收了我劈柴、倒恭桶都成啊!我不要工钱,只要一天两顿,有个睡觉的窝就成!”
华珠听她口音,像是福建那边的人,就走了过去:“你老家是哪儿的?”
两名侍卫一看来者是华珠,忙一改先前的倨傲,抱拳行了一礼。刚刚提督大人给表小姐穿披风、系丝带,他们瞧得一清二楚。八成啊,提督大人挺青睐表小姐的。
妇人抬眸望向眼前穿着粉红色云纹锦披风、皮肤光嫩、五官精致的美丽少女,只觉仙女儿下凡了似的,怔愣了许久,才回过神答道:“回小姐的话,我是福建人。”
华珠瞧她面善,便多了一分与她交谈的心思:“你这把年纪,为何会流落到琅琊来?家中可有亲人?”
提起亲人,妇人被冷风刮得僵硬的身体轻轻抖了起来:“我丈夫很多年前到京城谋差事,但不知得罪了哪一方恶霸,被活活打死了……我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两个儿子,可是他们……又先后战死了……大儿媳没多久也病死,二儿媳受不住苦楚,走掉了……族人说我不详,克了满门,就将我赶了出来……不得已,我才流落到了琅琊……”
克?为什么一个家庭的不幸,最终要由活下来的人承担?华珠的脑海里又浮现起那个曾经如云一般单纯美好的少年,问向妇人:“你儿子原先是哪个军营的?”
妇人拿出帕子,抹掉怎么止也止不住的泪水:“两个儿子都是琅琊水师的,听说叫什么……龙叫军……”
“蛟龙军。”华珠纠正她。
妇人忙点头:“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他们……是六年前战死的吗?”
妇人含泪点头。
死了一双儿子,一家的生活来源全都没了,可朝廷的抚恤金却迟迟没落到军属手中,这些贪得无厌的昏官!
她今日碰到的妇人只是冰山一角,在她看不见的地方,也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家庭,一边饱受着失去儿子的痛苦,一边又忍受着贫寒的蹉跎。
华珠蹲下身,定定地看着她:“朝廷新派来了一任水师提督,他……”
妇人感激地欠了欠身,“实不相瞒,这不是我第一次来琅琊了,以往每次朝廷任命一个提督,我就会来琅琊一次,但没有人肯见我。你一定以为我是为了抚恤金,不,我不是的。我儿子为朝廷战死,但烈士墓碑上没有他们的名字……我……我只是不想他们死得不值得……”
烈士墓碑上没有名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并非编制内军士。
华珠遗憾地看了妇人一眼,叹道:“你随我来,不过,主子奶奶要不要用你,就不是我能保证的了。”
妇人忙后退一步,磕了个头:“多谢小姐!”
清荷院的正房内,年绛珠盘腿坐在炕头,冷着脸不理颜博。
颜博眼神一闪,苦肉计搬上,摸着后背叫道:“哎哟,好疼啊。”
年绛珠的睫羽一颤,扳过他身子,撩起短袄和亵衣,看向背上的一个长条印子,蹙眉道:“都两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消呢?”
这是颜博被满月案的变态杀手掳走后落下的伤势,一开始有些肿、有些疼,后面消肿了也就不疼了,但印子一直没消。
长长的一条,不像被刀剑所伤,倒似为硬物所压。只是两三个月,别说印子,连伤疤都该退化了才对。好在这印子不打眼,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而且是在背上。年绛珠知他故意,便揪了揪。
“疼!”颜博就势转身,扑进年绛珠怀里,边“哭”边解了她扣子。偶尔她也喂喂儿子,奶还没断,颜博就闻到一股奶香,浑身都燥热了起来。
到底是彼此欢爱过的身子,轻轻一撩拨便有了反应。但年绛珠依旧生他的气,才没这么轻易原谅他。年绛珠一把推开颜博,扣紧了扣子,并瞪着他道:“想睡女人了院子里多的是!别找我!”
颜博砸了砸嘴,忍住快要爆发的欲望在茶几对面坐下,软语道:“还生我气呢?我不是故意的,我哪儿知道晴儿会怀孕?还不是你推我去她屋里过夜的?”
年绛珠恼火地撇过脸,男人啊,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她是在怪他睡了通房丫鬟吗?她可没这么小肚鸡肠!
“我……我这人笨,我哪里做错了,你就告诉我,不要憋在心里,你难受,我也不好受。”颜博放低了姿态,拉着她的手说道,“书房真的好冷,绛珠。”
年绛珠甩开他的手:“你怀疑我想打掉晴儿孩子的时候,怎么没想想书房冷不冷啊?”
她根本都不知道晴儿怀孕了,又怎么打掉她孩子?即便她真的要打,难道不会选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比如下药,比如给她鞋底抹点儿油?非得用一支金钗构陷她盗窃?太曲线救国了!谁干?
颜博赶忙道歉:“我混蛋!我混球儿!你这么善良大度,我不该怀疑你的,我那晚一定是脑袋被门给夹了!你看,像这样!”
说着,颜博走到衣柜旁,把脑袋伸进去,开始关门,“痛”得嗷嗷直叫。
年绛珠又好气又好笑,娇喝道:“行了!少给我来苦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