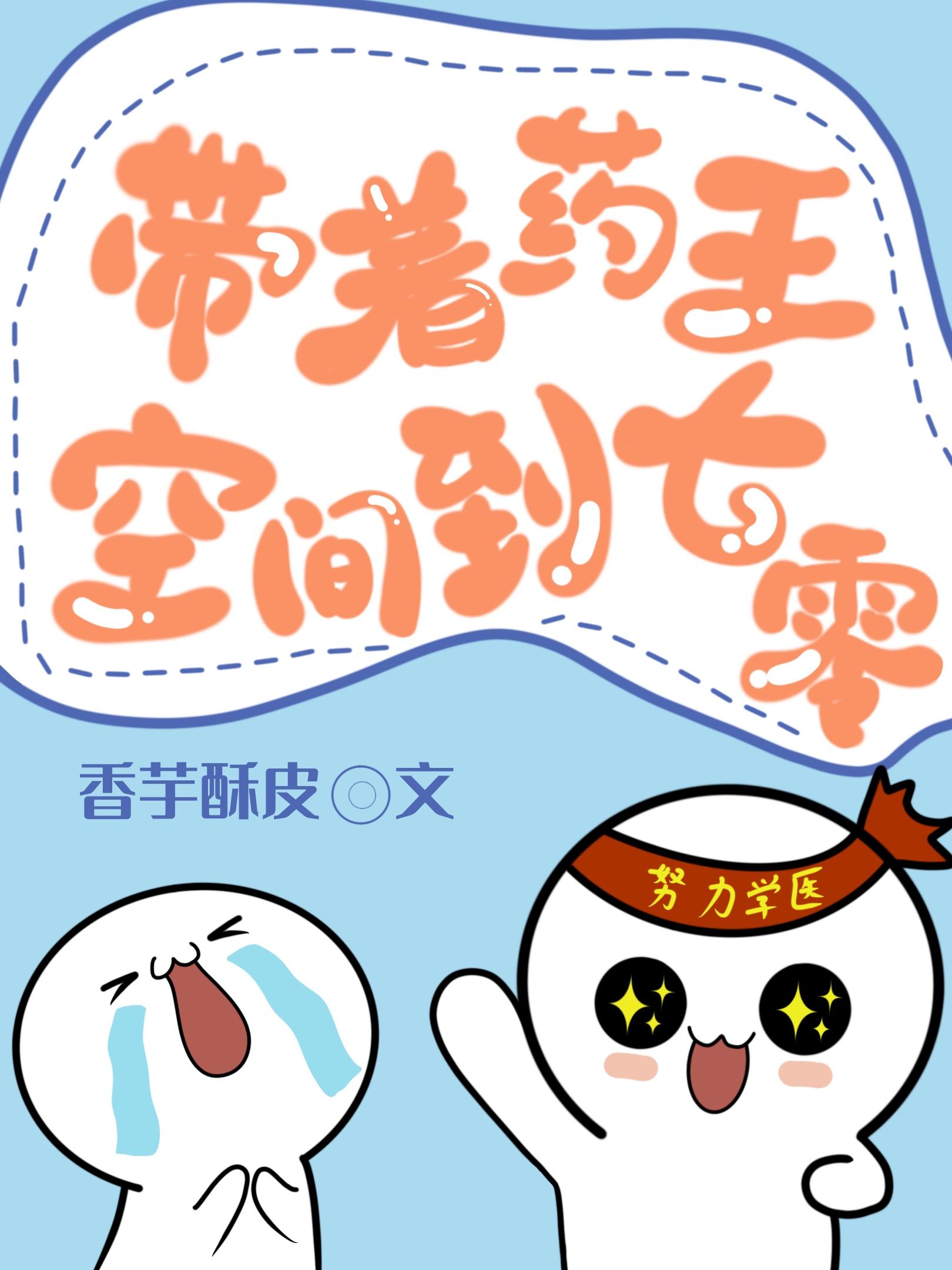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衣冠不南渡百度 > 第184章 陛下之过也(第2页)
第184章 陛下之过也(第2页)
“您何以发笑呢?”
“大肆囤积粮草,看来大将军是命不久矣了啊,父亲这是准备转攻为守,跟大将军耗时日”
毋丘甸看向了面前的钟会,“早在我被抓住的时候,我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只是怕耽误父亲的大事,不敢赴死,今日终于撕破了脸,那我也不必再等待了。”
“不要想着能通过我来要挟父亲,在父亲的眼里,我被抓住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钟君!”
“我听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我们父子甘愿为大义而死,愿行舍生取义之事!”
“您的父亲也食魏禄,何以要坏自己一生之清名呢?!那司马师,篡国之贼也,无功德与社稷!司马昭更是不堪,为他爪牙,乃是自寻死路!”
“我听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钟君高洁之士,还望能慎思,勿要遗臭万年!”
毋丘甸大声着,缓缓站起身来。
“我不愿受辱,请赐我利剑!”
钟会出神的看着他,正要伸出手解下腰间的佩剑,猛地想起了自己的来意,赶忙停了下来。
“毋丘君且慢!我不是来杀你的!”
毋丘甸一愣,“那阁下是为何而来?”
“我是来放了您的。”
钟会笑着道:“方才您的实在太令人动容,我险些都忘了来意,来,毋丘君且坐下来,听我详细跟您”
毋丘甸不太相信这番话,“来放我??”
“这又是什么诡计?想诈称我已降?还是想坏我父亲的名誉!”
看着如此警惕的毋丘甸,钟会苦笑了起来,“您就是不相信征西将军,也该相信我,且坐下来,听我与您。”
毋丘甸将信将疑的坐了下来。
钟会便将最近所发生的事情详细的了出来。
“大将军病重,司马家分裂,已经是无力再与镇东大将军交战了”
钟会完,看向了毋丘甸。
毋丘甸一脸的不屑,“我不信!”
司马家的信誉实在太差,而且毋丘甸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自己都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你现在跑进来司马师有意跟自己父亲讲和?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我父亲恨不得将司马师拨皮抽筋?
钟会也不生气,笑着道:“若是不信,您可以与我一同去见皇帝。”
“你们是想栽赃我弑君?!”
毋丘甸再次警觉。
看着面前怎么都不相信的毋丘甸,钟会揉起了自己的额头。
信誉太差就是这样的下场,根本不相信。
钟会站起身来,“算了,您若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反正话已经给您带到了,您想去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出洛阳,洛阳之内,您去哪里都无碍。”
“话已至此,告辞!”
钟会不准备继续劝毋丘甸了,这完全是浪费时日,无论自己什么他都觉得其中有诈。
钟会真的离开了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