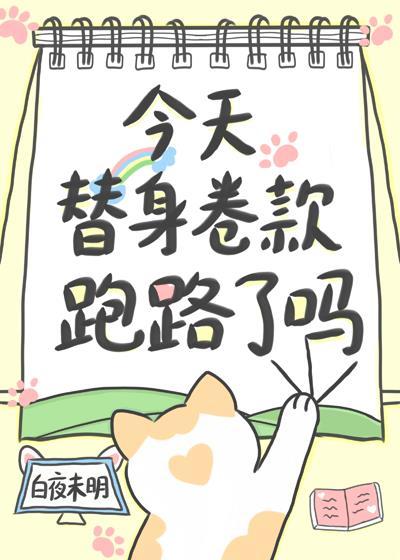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闺中媚重生嫁权臣 > 124 耐心(第2页)
124 耐心(第2页)
闻砚终日坐在轮椅上,眼下身姿挺拔、俊逸如松地站着,黎蔓才觉他原来比自己高出大半头。
黎蔓这时候顾不上什么生辰礼被人抢先不抢先了,“你!你这……”她下意识地盯着闻砚的腿眨了两下眼睛,又扭头看了看自己父母的墓碑,在即将掐上自己的掌心时看见对方朝自己走来,动作不快但也很是优雅。
“可是吓着了?”闻砚抬起提着食盒的手朝她晃了晃,他垂眼看了下自己的腿,再抬起眸子时只温和一笑,“原是想等彻底好了再告诉你。”
“你这腿是怎么回事?”黎蔓瞠目结舌,反应过来眼下并非梦境后不由得又惊又喜。她不住地打量着对方的腿,“什么叫等彻底好了?可是有法子治了?”
说完她又觉得有些废话,对方不正稳稳当当地站着?黎蔓被这个巨大的“事实”砸得有些懵,满腔好奇使得语都快了不少:“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当年替我诊治的太医替我配了副药,服后能使人双腿失去知觉、无法力,每日服一剂。上一次配的吃完了,还没来得及去配新的。”闻砚耐心解释,“完全好不了的消息主要是让汪家和左相放松警惕,太医说筋骨虽确实伤得厉害,但仔细将养后应该还能当个文弱书生。”
黎蔓很快就听懂了——也是,从山崖上掉下来,即使底下有暗河,受的伤肯定也非同小可,哪里能这么容易恢复如初呢?饶是如此她还是替闻砚高兴,想了想道:“书生有三寸不烂之舌,实在不容小觑。”
说话的人暗暗打定主意:回府后请越姐姐给他看看,越姐姐的母亲来自苗疆,听说有好多稀奇古怪但颇有成效的东西。再者越姐姐是军医,对接骨续筋格外擅长,没准儿有更好的法子呢?
黎蔓越想越觉着不错,脸上顾盼生辉,忽又反应过来,“你这腿既然没大好,站久了会不会不舒服?”她停顿片刻,“我把轮椅推过来,你坐着罢。”
“不妨事,”闻砚摇摇头,自那三层的食盒里取出吃食放于墓碑前摆好,又取出两支香来,“我先前坐着轮椅到这碑前来,已是失了礼数。他们是你至亲,我将你照顾得不好——更该向国公和国公夫人请罪。”
他把香点燃了,分出一支给黎蔓。
“蔓蔓同爹娘说会儿话,我在旁边赔礼告罪,如何?”
冬风不暖,然天高云淡,碧空万里。
两人伏拜下去。
闻砚本就不信神鬼之说,这些年来身陷囹吾,连去氏家庙祭拜都浑不在意——若真能保佑后辈,那为何我会陷入这般困境?若不能保佑后辈,那在先祖灵位前说多说少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今日祭拜的是她的父母,终归是不一样的。
闻砚阖眼,垂潜心默念几句。
他跪着,觉得黎蔓应是有许多话想和国公及其夫人说的。事实好似确乎是这样的,因为女子良久都未起身,细看还能觉她的肩颈正微微颤。
其实黎蔓并没在心里说太多的话。虽然以爹娘的性子,他们不会介意自己还没能替他们报仇。可她想到自己前世直到身死都很是浑噩,自觉羞惭。又觉得不用为自己求什么,只盼着他们和兄长能远离苦厄……如果可以,还望入梦来见。
然后……然后说什么呢?
黎蔓抿了抿唇,本着自己原先打定带闻砚来的主意,带着一些吞吞吐吐的羞涩,在心底无声开口,说了些话。
闻砚安静陪着,直到黎蔓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直起身来。她眼底的红色消退大半,显出几分恬静的意味。
他的腿到底没有好全,跪拜之姿也不利于气血通畅,加上依旧需要掩人耳目。是以走了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