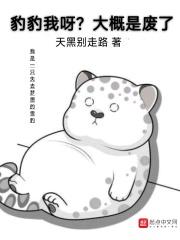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但愿爱我如生命 > 第56章(第2页)
第56章(第2页)
“坐吃山空啊庄总。”亏我还急他人所急。
庄盛的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烟盒下面的ipad下面的《男人装》下面,露出“喜爱”传单的一角。我赏罚分明:“帮单喜喜打广告呢?这多好,陪她发发传单多有建设性,陪她纹哪门子身?可真有你的。”
我这么一说,庄盛下意识地抻了抻袖子,盖住了大半个手掌。
我灵光一闪:“庄盛?不是吧?你不是陪她去纹身,而是陪着她一块儿纹身去了?”
庄盛蹭地把手背到了背后,给我挺出一副贞烈的德行。
我向他逼过去:“给我看看。该不会是什么青龙白虎吧?可你还是比较适合小型哺乳动物或者昆虫……”
“非礼,非礼啊!”庄盛的防御动作类似狗刨,高频率之下我插针都难。
可他的袖子自觉地往下褪了褪,有那么半秒钟,他手腕内侧露出了半个“心”字来。
不是沁,而是心。那么,就还有心脑血管,心肌梗塞诸如此类的注解,又或者,叫张心李心王二麻心的女性,估计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一个缩头,看见装作没看见,收兵。而庄盛累得气喘吁吁,吐着舌头找水喝去了。
单喜喜致电庄盛,我没接,但却把庄盛的手机拿在了手上,铃声结束后,我打开了他的短信草稿箱。去伊犁的前一夜,庄盛用短信作弄了我,而这时他的草稿箱轻轻松松就给我翻了案。
这些是庄盛一字一句敲上的:是啊,老子就是喜欢你,老子不但喜欢你,还想装圣人帮你,不然你以为老子为什么追喜喜?老子就是想和她配成双,好成全你和高帅富也配成双。老子也想忘了你,不然你以为老子为什么炒你鱿鱼?老子正在忘了你!
庄盛喝了水回来,还就手给我端来一杯,他缺心眼儿地接了个满,走道儿像飘似的小心翼翼。那时我早把他的手机放下了,指纹都擦干净了,然后皮笑肉不笑地撂下了一句“老娘不渴,谢谢了”,便离开了。
周森被关押的监狱,在北京的郊区,我开车往返一趟,要三四个小时。我答应过他不去看他,但不代表没有资格去看那铜墙铁壁。
我每每带足了吃的喝的,到了那儿在车上坐上小半天,吃饱喝足后再返程。有一次在吃蛋炒饭的时候被呛了一口,因为咳嗽而落了两行泪,其余几次我都顺利过关。
看见刑海澜我并不意外,她从进去到出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出来后她才看见我,等她走近了些我才注意到,她的睫毛膏防水效果并不好。
“怎么不进去?”当初在法院之外,刑海澜也是这么问我。
“之前答应了他的,不进去。”我下了车,“他还好吧?”
刑海澜向我逼近了一小步,破天荒地失态:“没想到你能撑这么久的,没有哪个女人能撑这么久的。”
我后背贴在车门上:“我倒是想到了。”
“呵,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自信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时有记者模样的人靠了过来,刑海澜从包里掏出墨镜戴上,便要离开。我两步跨到她身前:“记者还会怕记者吗?还是说即便就我这么一个观众你演戏也要演全套?这些天,当红女记者和锒铛入狱的充满争议的青年才俊的绯闻,是你一手炒作的吧?”
刑海澜刷地摘下墨镜:“你人倒是不笨,但也不过是初生牛犊,和人竞争总要有些资本的吧?毕小姐,请问你有什么资本?”
再去到孔家时,在楼下我还刻意抬头看了看我之前来造的孽,那玻璃自然早就换了新的,剔透得和左右两边的一比,鹤立鸡群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