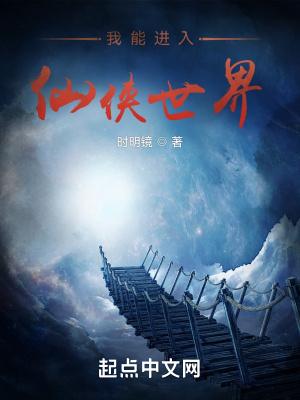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妾妻同娶 > 第107章(第1页)
第107章(第1页)
>
“公子与我商量过了,若你愿意的话,公子还是可以纳你为妾的。”
“我不愿意!”吱吱抬起头,一下就打断了悠悠的话,泪水在她眼里蒙了一层厚厚的水障。
“吱吱,你不要有心理负担的,修儒满月那天,你只差奉了茶便是我的妾室了,我们可以尽数忘记这之前不开心的事情,我们把那杯茶补上,你就是我的……”
“我忘不掉!”吱吱把目光哀伤地调向赵士程,公子一袭华贵的衣袍衬托文秀的书生气质,美好端庄地坐在榻上,却是像一尊佛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吱吱红愁绿惨地摇着头,缓缓道,“公子,你是男人,你的家不该成为收留受伤女子的善堂,除了姐姐,大夫人和三夫人都把太多故事带进了赵府,让公子你活得抬不起头来,吱吱不能和她们一样,吱吱做不到,所以我嫁,我愿意嫁给陆堂。”吱吱艰难地说出了那个“嫁”字。
“可是陆堂他那么伤害你……”悠悠也满心矛盾。
“若我嫁了他,那便不是伤害了,公子待我再有心,我也不过是赵府的一个妾,可是我嫁给陆堂,那就是堂堂正正的妻。”吱吱的脸上流露无比坚毅的神情。
赵士程默默走上前,从地上扶起吱吱,握了她的手,目光深邃地望进吱吱的眼睛,动容道:“你若心意已决,那便记住,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兄长,赵府便是你的娘家,你不再是一个不起眼的丫鬟,你是赵府的千金二小姐,我给你取个名字叫赵若雨,可好?”
“谢公子赐名。”吱吱落着泪福了福身子。
“既然改名赵若雨,就要改公子的称呼为哥哥了。”
吱吱听从悠悠的建议,重新福了福身子,期期艾艾道:“多谢哥哥赐名。”
赵士程扶起她,沉重地叹了口气,对悠悠道:“悠悠,那你就好生替若雨准备嫁妆吧!赵府嫁女,不能失了排场。”
“是。”悠悠点了点头。
赵士程蹙了眉,再深深望一眼面前梨花带雨的若雨,松开了一直握着她的手。这个丫头跟在他身边多年,勤恳伶俐,他都没有正眼看过她,今日才发现不知何时,这丫头竟然长成了大女孩,亭亭玉立,芳华豆蔻,他还差点纳她为妾,可是世事变化何其之快,她做不成他的妾,他却成了她的哥哥。此时此刻,看着若雨眉目含愁,泪流满面,赵士程心中万千不忍,他对若雨是没有爱情的,可是为什么心里却这般难受与怜惜呢?
而若雨,望着公子纠结的面庞,心里说不尽的酸苦。她突然欣慰于自己做出的决定,因为她决定嫁陆堂,公子才会这样正眼看她,目光里才有了一些疼痛是因为她。她深吸一口气,颤声道:“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让我做你一日的妾?一日之后,吱吱便不再是吱吱,而是永远的若雨了。”
赵士程的眉峰动了动,他踟蹰地看着若雨。悠悠了解他的心意,便对着房外大声道:“雨墨!”
雨墨进来了,见房内赵士程和若雨神色黯淡,并不敢欢天喜地,低调地看着悠悠,“小夫人,有什么吩咐?”
“在湖边水榭摆宴,去如意轩通知三夫人,说公子晚上要吃团圆宴。”悠悠给了雨墨一个振作的笑容。
雨墨慌忙道了声“是”,便躬身退了出去。
入夜,赵府花园的池子里点满荷花灯,湖边水榭也是彩灯高悬,一时之间,湖里湖外灯光闪烁,辉映得一池的荷花分外娇艳。天上几颗离乱星子,一轮皎洁皓月,若没有近在咫尺的陆赵两家联姻的阴霾,这一夜无疑是花好月圆人幸福。水榭里,丫鬟上了酒菜便悄悄退下,赵士程坐在大理石圆桌的主位上,围着他而坐的是三个静美的女子:悠悠、圆仪和若雨。还有一个空着的座位上也摆了酒杯和筷子,那是留给唐婉的。赵士程望着桌上每一道菜都寓意着团圆喜庆,酒也是不饮先醉的嫣红,三个女子更是花一样的姣好容颜。此时此刻,他把目光停在那空着的座位上,若唐婉还在,若吱吱不必嫁去赵府,若圆仪与悠悠之间冰释前嫌,他也该是世上最幸福的男子,可是月有阴晴圆缺,偏还是一日圆,其他时候都是缺。他甩甩头,告诫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沉重的缺憾,就让时光停留在这一刻,这一刻不管有多少不如意,都暂且搁置一边,不去细想。
赵士程举起了酒杯,对眼前的三个女子说道:“今夜,我们在这里吃顿团圆饭,不管明天你们是什么身份,今夜,你们三个都是我赵士程的妻妾,在我眼里,你们都一样美好和珍贵,我们共饮一杯吧!”
悠悠、圆仪和若雨也一齐举起了酒杯,不管三人之间有什么恩怨,但因为赵士程言辞恳切而又愁闷,她们也就各揣心事,共饮一杯。这一夜,悠悠、圆仪和若雨三人都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一杯又一杯地饮着赵士程敬过来的酒。因为心情沉重,酒特别容易醉人,赵士程一直含着醉意朦胧的笑。而悠悠看着他强颜欢笑的神色早就有泪水不停地往眼眶上涌,她只是使劲强忍着,若雨更是时不时就甩甩头,逼回自己的眼泪。圆仪始终不动声色,若雨的悲伤,她分担不了,也不愿分担。今夜,虽说是团圆宴,她却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酒过三巡,赵士程道:“圆仪,你不是弹得一手好琴么?今夜,应个景,若何?”
圆仪哪里会推脱呢?命了玢儿去取琴,琴取来了,便在湖边摆下琴桌,调试了一下音,便纤手弄音,奏了一曲《高山流水》。赵士程和悠悠、若雨站在水榭里,高处俯瞰,只见清凛的月光下,圆仪裙袂飘飘,夜风撩起她的秀发拂在面颊上,再加上荷塘月色、筝声袅袅的背景,不禁美轮美奂。
见赵士程听得入迷,悠悠微笑着道:“今晚月色甚好,池塘里荷花又开得旺盛,不如让雨墨划只小舟过来,夫君和若雨去池塘里边赏藕花,边听筝曲,岂不妙哉?”
赵士程也来了兴致:“易安居士生前就有‘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佳句,我们也一起下到池塘里,看看有没有鸥鹭逮着几只。”
悠悠拉了若雨的手放到赵士程手里,温婉道:“我就不下池塘里去了,我得去看看修儒,若雨陪夫君捉鸥鹭去吧!”说着,悠悠给了若雨一个鼓励的笑容,“我与公子来日方长,只是若雨,只有今夜,好好珍惜吧!”不待赵士程和若雨挽留,悠悠就起身离开了。
池塘里,雨墨已经划了一只小船过来,停在岸边,招呼赵士程道:“公子,小夫人吩咐的船,奴才给您备下了。”说着雨墨从船上跳下来,留了木浆在船上。
圆仪停了筝声,起身狐疑地看着水榭里的赵士程和若雨。赵士程已经拉了若雨的手走下水榭,走到湖边,对圆仪道:“辛苦你再为我和若雨弹筝一曲。”
圆仪抿唇点头,目送着赵士程扶着若雨上船,二人相对而坐,一人一只木浆,轻轻划开宁静如玉的湖面。圆仪的筝声重新响起的时候,小船缓缓地向和花丛中荡去。赵士程带着些醉意,看着若雨,微笑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