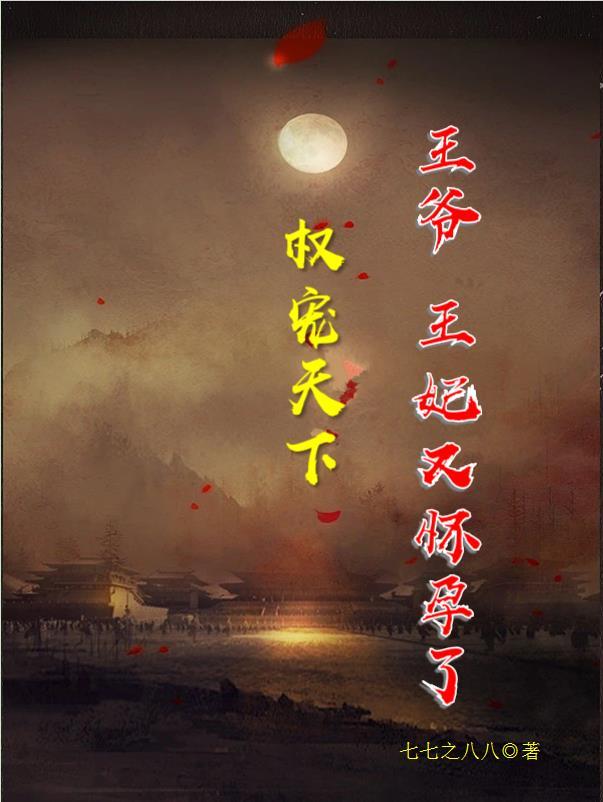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宗女荣华录 > 第108章(第1页)
第108章(第1页)
陈四回到自己院子,身边一个丫头便跟了上来。“四小姐,这是春姨娘叫丫头送来的,说这样式配您。”
陈四低头看去,是一支翠滴碎珠簪子,价值不菲。“你们都下去,不要跟过来。”
陈四心里烦乱,进了书房后屏退了丫头们,压抑着情绪走到桌边,精致的五官此时已没有任何暖意。她生得极美,就如她的亲娘春姨娘那般,莫说男人,便是女人,看了一眼都不忍移目。虽然她继承了亲娘的美貌,却没继承春姨娘的脾性。
她从小就好强,琴棋书画,样样都要做到最好。她事事按着嫡女的标准要求自己,她希望自己既有姨娘们吸引男人的资本,也希望自己能有正室太太那般端庄得叫人尊敬的气派。
她觉得她做到了,她是小有名气的才女,她在家里也从不听从姨娘的撺掇,不会拉下面子去跟陈大老爷讨要什么。她也从不会像陈五那般,跟着陈大太太看脸色,她觉得自己很完美,但是,她还少一样。
就如今日在老太太屋里发生的事,她希望自己不去在意,但还是会不自觉地拿自己与陈六比较。这就是嫡女,有亲娘的嫁妆,自己的亲娘春姨娘有什么?她只有拉下脸面跟陈大老爷陪尽好话,才能得到些好处。
可悲,她既羡慕陈六,又强迫自己不去想。她既晓得春姨娘一片爱女之心,又觉得这种事情让自己难堪。她既觉得作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不应该在意身外之物,又无法克制自己,去想陈六亲娘留下的嫁妆。
她以后会做正室,她的子女便是嫡出,她不会再让自己的儿女受这种白眼,受诸如陈二太太那般言语。
初荷渐渐平静下来,慢慢坐到桌边,自己动手研了墨。随着腕子的旋转,墨香渐渐荡出来,充斥了满屋子。
这是上好的沉香墨,是陈大老爷给的。陈大老爷常在春姨娘屋子里歇下,每每服侍后,春姨娘总会提到初荷,提她的长进。陈大老爷对这个女儿是给予厚望的,也知初荷出众,听到春姨娘说初荷的字又有了长进,转天便赏了这上好的沉香墨来。
初荷起初很是高兴,待得后来晓得春姨娘提到这事,心里便不知是何滋味。
按理说,自己父亲给东西,也不是丢人的事,但是初荷就是觉得不舒服。想到春姨娘温纯软语的模样,初荷心里就难过。
陈四这头回到自己院子,当下心内五味杂陈,那边的陈大太太回去后也是愁眉不展。
她是庶女,出嫁时没有丰厚的嫁妆,好在执掌陈家中馈多年,又管着初容亲娘的嫁妆,这才从末微开始,一点点左手倒右手,一针一线地陶登出来一笔数目不小的银子。这银子,陈大太太都是要留给自己儿子的,作为自己的私房。
陈家公中的银子,一来数目有限,二来有那么多人盯着,基本很少有做手脚的地方,唯有初容亲娘的嫁妆,白放着的银子和每年都有大笔出息的庄子、铺子,都是自己一个人说的算。这么些年来,庄头和铺子掌柜的,只要是原本初容亲娘的人,都被自己以各种理由换掉了。
陈老太另有心思
陈老太另有心思
每年从这些产业中倒手出来的银子,就是一大笔数目,如今眼看着要交出去,陈大太太只想呕一口血出来。
白花花的银子,就这么断了进项,陈大太太越看账册越是眼红。奈何老太太此事提得快、要得急,本以为那番舍出一根极品老参,老太太已是不想闹了,只不知又怎地想起此事!
事已至此,陈大太太也无法,便不甘心地将自己平日里做的花账取了出来,关起房门细细对过,哪怕老太太问起,自己都能一一对答之后,这才松了口气。
这日,众人请安离去后,陈大太太将账册恭恭敬敬递上,又取了初容亲娘的嫁妆单子附上。本想留下来等老太太问话,却不料这位难伺候的婆婆一挥手,歪了歪说道:“今儿乏了,先放着吧,你是个仔细人,又会经营,我还能信不过你!想来这么些年,小六她娘那些上好的水田和旺铺,也能出息不少。”
陈大太太一肚子想好的说辞堵在肚子里,老太太却不接茬。若是当场对着讲了还好,自己这一离开,老太太看着账上的数目,生起气来,自己再解释就晚了。再说,老太太方才将话说得太满,好似这账目若是不漂亮,就是怪事似的。
事实上,这账若是不好,也确实是自己做了手脚。陈大太太还欲再说,便见老太太已经歪下去了,只好退下。一路忐忑回到自己院子,一直几日后都没什么动静,陈大太太愈发不安了。
这日,陈大太太到了福寿堂时,便听里头欢笑声不断。
“你个促狭的丫头,就拿你表哥逗趣儿,小心你表哥恼了你。”老太太笑出了眼泪,指着初容说道。
初容见老太太心里头高兴,跟着说道:“表哥才不会恼我,表哥性子最好了。”
祖孙俩说得开心,一旁的窦柏洲则微微低了头,抬眼偷看初容的侧脸。少女的皮肤莹莹有光,一颦一笑似乎都带了那么一股子惹人怜的模样。窦柏洲只看了一眼,赶忙低了头。
陈老太太最喜这个侄孙,一眼瞟见他的眼神,笑容便顿了一下,随即又笑得更开怀。此前还不曾多想,如今自从拿到初容亲娘的嫁妆之后,陈老太太才算动了心。五千两银子,外加上好的水田和旺铺,若是都成了窦家的,那该多好!
窦家祖上也曾兴旺过,如今却是有些日薄西山之势,好在这个侄孙是有出息的,眼看着必有成就。若是能亲上做亲,也算为窦家添了臂膀,初容若是能将嫁妆带进窦家,日后窦家子孙便是受益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