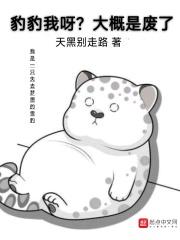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秋以为期主要讲什么 > 第142章(第1页)
第142章(第1页)
>
电梯忽然启动了,时安知惊慌失措,想要挣扎,却被黎玖牢牢扣在怀里。甚至滑腻下。身里头还挺进着一根硬度不减的无耻玩意儿。湿软肉穴不由自主地猛力抽缩,夹得黎玖低哼一声,咬了咬时安知的脖子,一点脸都不要地安抚舔弄。“没有人,不怕啊宝宝。”
哗啦一声电梯门打开了。时安知五雷轰顶地闭上了眼睛,黎玖在他耳边闷笑。一边笑一边就这么抱着他往外走,时安知整个人要炸了,小腹之内疯狂颤抖,浑身上下都恨不能缩成一个原地消失的点,胳膊和腿都死死抱紧了黎玖。
就在这羞愤欲死的当口,黎玖亲他的脸,架着他稳定缓慢地一步步迈开了步子。说:“没有人——乖乖,全公司我放了一天假。”
时安知已经出窍的灵魂战战兢兢地还了阳,他睫毛上沾着泪珠,睁开一线去瞄了一眼左右,果然偌大的办公间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来过瑞德中心,一个个正装男女客客气气地向他躬身,叫一声:“时叔。”
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但是他不由自主地就能想到那些理当在此的人,他明白过来黎玖的一肚子坏水了,哼唧着从紧紧攀住对方肩膀的手臂里分出一只手去拧小九的耳朵。
“混账玩意儿……跟谁学的……嗯!”
黎玖的回答是提腰往上挺了一记,时安知股缝间淋淋漓漓滑下来的都是腥臊微凉的体液,其中包括他自己在电梯里射出来的那一发。抱持着下半身这体位相当耗费体力,但也深得不能再深,时安知感觉自己肠肚都要穿了,他拢紧大腿夹住黎玖的腰,低喘着抱住了对方的脖子,浅哼道:“去、去你办公室。”
玖安总裁办公室的那张巨大书桌是从德国进口的,一贯以品质绝佳沉重稳定著称。在这一天,接受了全方位的各种考验。最后,时安知是一双腿架在老板椅扶手上昏沉睡去的,上半身衬衣都还没脱,从衣摆裂口处露出了指痕斑斑的平坦腰腹,以下是红白印痕交错的大腿,耻毛间黏成了绺,小小十射过了三四发,末了委顿得非常可怜,像只害怕的鸟儿似的垂在胯间。
黎玖到底心满意足了,餍足快活地休息了一阵子,一颗颗剥开了湿透几重的衣冠禽兽三件套衣扣,脱光了然后轻手轻脚抱起小十去附带的休息室躺平了睡。方才最激情的时候他也没脱衣服,只从胯间挺出一杆大枪,按着上身完整下。身赤裸的时安知反复压榨。他舔着唇想:这报纸上登的东西确实是挺有趣的,能学到东西。
以黎老板的求知欲,之后分别专门探讨了一下中学生离家出走后在公园被找到、世界名猫博览会等等新闻,时安知到底在某一天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他黑着脸抽走了所有奇怪(?)版面,只给黎玖看密密麻麻全是数字的经济版。
这一次,黎玖在他脊上用舌尖描绘出了股市走势图……
总之,在读书认字这个问题上,他们互相磨合了好些年。
(九)
这一年的大年初一,黎玖正式收边以秋为干儿子。
在这之前,边以秋已经隐隐然成为了他手下的第一人。这个方才弱冠之年的小子年轻、热血、镇得住场子,更对他忠心耿耿。在挡枪事件结束之后,黎玖就已经纵容手下放出风声,说小秋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边以秋自不敢当,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地位,别说人肉沙包,就算是黎玖开口要他死,他也是没办法拒绝或者逃避的。
只是他没有想到,进了腊月以后的某一天,时安知会来问他,愿不愿意做九爷的儿子。
“啊?”边以秋是懵逼的。
时安知却是温和地笑了笑,叫他坐。边以秋站在煦园那座体量巨大的藏书室里,只觉得自己跟这满屋子的书香十分不搭调。但是面对的是时叔,于是他规规矩矩地站好了,惊讶了一声以后,看着时安知发了半分钟的傻,然后开口问坐在书桌后面的男人。
“为什么是我呢?”
“九爷没有孩子,以后也不会有。你母亲去世多年,父亲……也没有。他很喜欢你,这还不够吗?”时安知看着边以秋说了这么一串,末了思考了一下又补充道:“但你如果不愿意那也没关系,我只是先来问问你的意思。我可以保证,无论你是否同意,不会影响到你在玖安的一切。”
边以秋隐隐觉得这一长串话里有哪里不对,但是时安知看他的眼神温柔又诚恳,他低下头想了想,觉得以自己这条烂命,实在没有什么可被谋图的——再说了,向他征求意见的是时叔,打算收他做儿子的是九爷。这两个人就算是要他的命都没关系,更别说是要他叫一声干爹。
于是他抬起头痛痛快快地给了句话:“行,那我从此也是有爹的人了。”
时安知在书桌后露出了非常欢喜的笑容,那眼神看得边以秋心底一软。他莫名地想,如果收我做儿子的是您多好。
大年初一,煦园里按照南方人的规矩,开香堂、设酒果。边以秋对着坐在上首的黎玖三跪九叩,行大礼。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干爹。”
黎玖笑容满面,给他的见面礼是一张银行卡。边以秋乐呵呵地接下了,心里默默想,还是如今这时代好,以九爷的手笔,这卡里指不定是多少个零,但一伸手就能接下了。倘是过去,给银元金条现金,那可得有多累赘。
时安知站在黎玖身侧,也笑吟吟地递了个锦盒过来,边以秋受宠若惊,双手接过,下意识看了一眼黎玖。黎玖抬抬下巴示意他打开,边以秋小心翼翼打开了那个看着就颇有年代的盒子,里头是一枚满水满绿的翡翠平安扣。
边以秋有点发愣,时安知笑道:“当年从北边带出来的老物件,年纪大了,留着也没什么意思。借九爷的喜,贺一下秋少爷。”
边以秋立马觉出了手上这轻飘飘锦盒的沉重分量,他忽然鼻子有些发酸,耳边飘过一句多年前温柔无比的声音。那个人细致地替脏污狼狈的他清洗伤口,柔声问:“疼不疼?”
不知是哪里来的冲动,就着方才给黎玖磕头的锦褥,边以秋忽然双膝一折,对着时安知也跪了下去。他望着自己叫了好些年时叔的这男人,喉咙莫名有些哽,叫了一声:“时叔——”
他到底是把胸臆间翻涌的情绪压了下去,恭恭敬敬地对时叔也叩了一记。
“厚礼恩情大过于天,小秋收下了。”
之后梅夫人送了他套房子,梅筱然只比他大九岁,这时还未满三十。且虽然实质上是煦园的女主人,到底没有那一张纸,是以站在了玖安那一帮老弟兄的首位,无论如何也没有受他的礼。
新岁初始,一元更新。这天晚上应着煦园有喜事,在面南的那片海上放了足足半小时的烟花礼炮。边以秋被一帮凑热闹的弟兄灌了不少酒,他量很浅,到最后基本已快人畜不分,踉踉跄跄地被扶着去庭院一角的洗手间吐了半天。吐半截他虚弱无力地挥挥手叫小弟先回,自己过了半晌才慢慢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