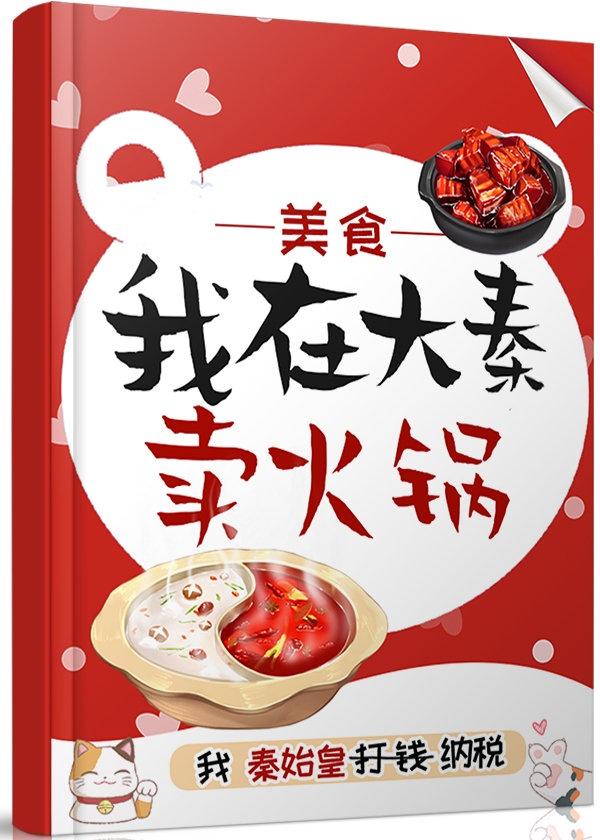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晋能控股集团2024年招聘公告最新 > 第105章 谯周大殿谏投魏地北王刘谌欲杀谯周(第1页)
第105章 谯周大殿谏投魏地北王刘谌欲杀谯周(第1页)
主刘禅正于大殿与群臣商议对敌策时,&xeoo忽见军哨慌慌张张跪爬入大殿中,待到御阶下便就噗通跪倒,大放悲声:“陛下,大事好了,魏军一路气势汹汹而,如今将近成都城下,成都危矣。”
只一句,便就惊主刘禅御座上猛然站起,慌乱失措面向群臣大呼:“该当如何?到底该当如何?”
然殿下群臣听闻魏军气势汹汹将至成都城下,一时间比主刘禅更加慌乱堪,皆都惊慌失措,彼此相视议论纷纷,一片骚动安。
“诸葛瞻出成都时,带走成都最七万兵,如今诸葛父子皆亡,所带七万军也折损大半,成都哪里什兵,如何抗敌?”
“错,成都兵大半皆被姜维、廖化、张翼聚集于剑门关抵御钟会,诸葛瞻父子所带七万军也折损十七八,成都确无兵!如此,该当如何?”
“若即刻御诏姜维前成都勤王!”
“可,万万可…如果姜维离了剑门关,岂放魏军全数进入成都,蜀汉岂亡更快?”
一时间,大殿上争吵埋怨声绝于耳。
然争吵埋怨一番,&xeoo又无任何对策。
主刘禅御座上看着群臣争吵议论一番&xeoo无对策,由大叹一声瘫坐在御座上。
主刘禅忽瘫倒,由惊到群臣,蓦然间皆都惊目主刘禅,然&xeoo皆都一言敢了。
大殿上忽死寂一片,静吓,哪怕此时一绣花针掉在地上,也会惊打上一个激灵。
“若就此弃了成都,直往南中七郡而去。”
就在大殿上一片死寂时,一位白臣&xeoo颤巍巍出列,大声直谏主刘禅。
虽羸弱白臣谏言,然忽在如此死寂大殿上蓦然而响,&xeoo犹如一个炸雷般直震大殿晃了三晃,惊群臣皆都直直看向谏言臣:“此谏也未可!”
果其然,只见主刘禅听谏忽御座上站起,声音颤抖而又惊恐:“去往南中七郡倒可,毕竟相父在时曾抚慰过南中七郡,时至今南中七郡军民皆都念相父恩德,朕既便去了,想必他们也会难于朕,朕也算暂时可避难所,只朕仔细思,毕竟南中七郡于成都东南,多贫瘠地,暑热难耐,民开化,朕若果去了,恐怕能适应得了南中七郡风土,又如何好?”
群臣听主意,乃想去南中七郡然又顾虑重重,犹豫决,其间便就又大臣赶紧谏言:“与其去南中七郡,倒如去投东吴妥。”
主刘禅听罢,&xeoo慌乱中蓦然站起,手指直谏群臣:“朕虽糊涂,然爱卿比朕更糊涂,难道他国中做天子者?”
话未落地,&xeoo只见光禄大夫谯周出列:“陛下驳对,此当斩!一旦陛下去了东吴,恐怕旦夕间便就了命,如何能去东吴坑?自古以从未寄居他国天子,即便东吴危及陛下命,然陛下一旦去了吴国&xeoo必然只能做臣子而屈于吴主下。陛下,请听臣言,自古治国道乃以大吞小,此乃世常理,故以此论,如今三国鼎立势,乃魏国最强大,待蜀汉倾覆,曹魏定然吞并东吴,而东吴比起曹魏&xeoo如同蜀汉般又如何曹魏敌手,如此想,只魏吞吴,绝无吴吞魏事,到那时,难道陛下又要随着东吴又再次称臣成?然陛下既然要称臣,倒如向大国称臣,一次受辱总比两次受辱要好。如此,陛下,斩杀此,断了投吴念。”
主刘禅看着谯周如此,方缓缓坐于御座上:“倒必斩杀他,他亦国而虑,过,朕听光禄大夫所言,倒如去南中七郡更妥当!”
谯周&xeoo连连摇头:“东吴投得,南中七郡更投得。”
谯周边说边就躬身御阶下,环视群臣罢缓缓再言:“南中七郡乃偏远毛地,虽自诸葛丞相起便就收了夷,然诸葛武侯收夷&xeoo大行以夷制夷道,只稳定蜀汉外围而图中原,故自诸葛丞相以,蜀汉从未从南中七郡征收过任何赋税,即便如此,自从诸葛武侯故去,南中七郡&xeoo见无可钳制他们,便屡生反叛心,由此看,南中七郡夷过因当初惧怕丞相武力走投无路才归顺于蜀汉,此乃一患也,更何况如今陛下此时前往南中,又岂能轻易走脱?一旦陛下弃城而去,魏军如何追?既然如此,等必要时时防范魏军追兵,千军万马如此大消耗,岂能贫瘠南中七郡所能负担?此乃患也。如此患在,时久了,夷必然要反叛!即便等虑深了,假定夷反,如果要逃往南中种地方,则需早做营,哪大祸临头时仓促而定?谋而动,只怕等出了成都未到南中时便皆频出变故,如此,能能到南中都未可知,如此,就可去南中七郡?臣觉妥,非明智举!”
谯周一顿说,主刘禅由面露惊恐:“依爱卿如此说,朕走又走得,投又投得,那该当如何?难道要朕在此坐以待毙成?”
“投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