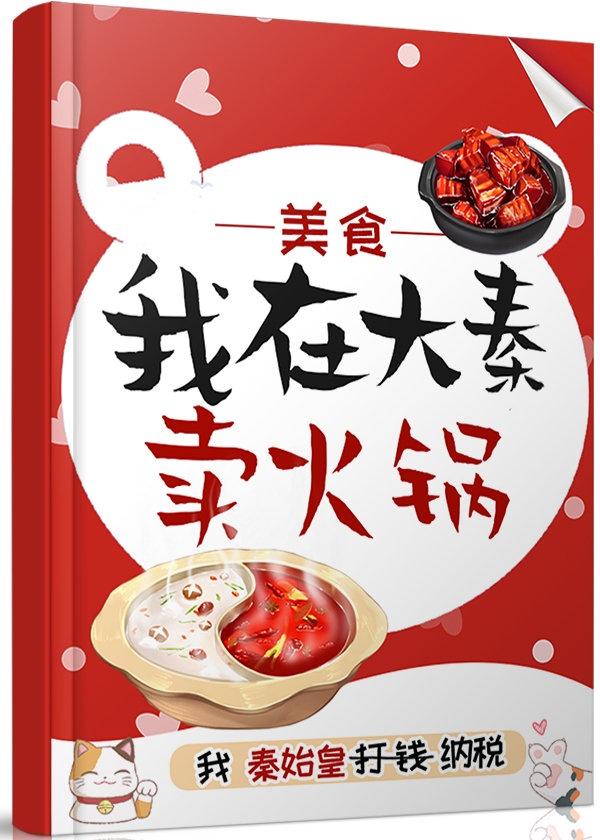《醉春九晏全文阅读》第24章
门没有关牢。我试着推开门的时候,碰到了他蜷缩起来的膝头。 他倒在门厅里,昏迷不醒。额角撞破的伤口鲜血淋漓,缓慢凝固。 他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只是沉睡,溺水般的昏沉。某些时候他会流泪,嘴唇轻微蠕动着,喃喃叫一个名字。那大概是一个名字,两个我听不懂的古怪音节。 我知道他是伤心过度。 醒来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脱了形。单薄衣物下裹着的仿佛只是一抹气息,一股苍白火焰般淡漠焚烧着的气息。高温沉溺的火焰,外焰笼罩着一圈似水的幽蓝。 没有举行葬礼或任何仪式。我陪他去取骨灰时问他,是否要做台弥撒。他用那种自拉塞尔先生去世后便不曾消弭过的淡然微笑凝视着我,轻轻说,“他才不信这个。”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颜?...